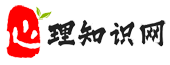有过这种风气。
褚人获《坚瓠集》中有《南风》一则,称此风“闽广两越尤甚”。袁枚《子不语》讲胡天保做“兔儿神”的一节说,胡天保既死,“逾月托梦于其里人曰:’我以非礼之心,干犯贵人,死固当然,毕竟是一片爱心,一时痴想,与寻常害人者不同,冥间官吏俱笑我,揶揄我,无怒我者;今阴官封我为兔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可为我立庙招香火。’闽俗原有聘男子为契弟之说,闻里入述梦中语,争醵钱立庙,果灵验如响,凡偷期密约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祷焉。”这是一派神话,但神话大抵有社会学的根据,井非完全向壁虚构。闽俗契哥契弟之说原是流传已久的。至冥间官吏的态度,只是嘲笑、揶揄而不怒,也正是阳间社会的态度;中国社会对于这一类变态的态度,一向也恰恰就是这样,与西洋的迥然不同。(西洋在拿破仑别制法典以前,同性恋的代价是死刑!)也惟有在这种比较宽大的态度下,同性恋才会成为一时一地的风气。
唐人小说卢全的《玉泉子》有《杜宣猷》一则下说:“诸道每岁进阉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阉以下,桑梓多系于闽,时以为中官薮泽。”这一层不知和后来契哥契弟的风气有无渊源的关系,年代相隔甚远,未便妄加推断,不过阉人容易成为同性恋的对象是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到的。
广州一带女子同性恋的风气是比较后起的事。海禁开放,广东最得风气之先,女子获取职业自由与经济独立的机会,从而脱离男子与家庭的羁绊也最早。说不定这其间有些因果关系。深居简出的女子容易发展同性恋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趋势,而这显然是某一时代的比较短期的反响了;大抵妇女解放的过程,男女社交的发
达,到达相当程度以后,这种风气自然会趋于消灭。关于广州女子的此种风气,记述得最肯定的是张心泰的《粤游小志》;张氏在《妓女》一则下说:“广州女子多以结盟拜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大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然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渐染至番禹,沙茭一带,效之更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风气坏极矣。”上文说女子同性恋的例子不易见于记载,祝氏妾与某氏女的同死,只好算是聊备一格;张氏的记载里虽无个别的例子可查,但事实上是等于千百个例子的总论,也可以差强人意了。
倡优并称,原是一种很古老的习惯,但称谓上“优”既列在“倡”后,事实上优的地位也并不及倡。据说在“相公”或“像姑”风气最盛的时代和地方,伶人对妓女相见时还得行礼请安。理由是很显然的,妓女是异性恋的
对象,还算比较正常的,并且一旦从良,生有子女,将来还有受借封的希望,而做优伶的男子,则可能成为同性恋的对象,那是很不正常的,在社会道德的眼光里永无洗拔的日子。在清代,优伶的子孙,以至于受逼被好的男子,不许应科举考试是载在法令的,就是很好的例证(说详拙作《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236—237页)。
上文的十二个例子里,有两个例子提到过伶人和相公的关系,一是以伶人而兼做相公的方俊官,一是有相公资格而被错认为伶人的春江公子。两例都发生在北京,以时代论,大概都在乾隆年
问,而从乾嘉以至清代未年,正是相公业最发达的时代,也就是陈森的《品花宝鉴》一书所描绘的时代,《品花宝鉴》是道光年间写的。至于在乾嘉以前,北京既久已为首都,此种风气当然不会没有,不过范围总属有限,只有少数特别的例子足以轰动一时罢了。读者到此,会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里的柳湘莲,于一次堂会演剧之后,被薛氏子错认为相公一流,妄思染指。不过这是说部中的例子,不足为凭。至于实例,则如崇祯年间从陕西到北京的宋玉郎,说亦见钮诱《觚賸》。又如清初从苏州人京的王紫稼,便是当时的诗人如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陈其年等争相歌颂的王郎。后因纵淫不法,被置于法。尤侗的《艮斋杂说》说:“予幼时所见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年三十,游长安,诸贵人犹惑之后李琳枝御史按吴,录其罪,立枷死。”徐釚的《续本事诗》也录其事。吴伟业《梅村集》中的《王郎曲》最为后世艳称,曲中有句说:“王郎三十长安城,老大伤心故园曲,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剪水清如玉;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玉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顿息”也足见王郎的魔力了。王紫稼的事,亦见后来梁绍王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我们还可以举第三个例子,就是乾隆中叶自四川金堂入京的魏三,一作韦三,也曾经风靡一时,当时人的笔记如礼亲王的《啸亭杂录》之类甚至说:“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则不以为人。”他是现在旦角梳水头和踩高跷的发明人。魏三生平,详吴太初《燕兰小谱》。沈起凤《谐铎》的《南部》一则里,对他有很严厉的评斥。
不过伶业与相公业兼营的风气,终究是到了乾嘉以后才盛行。清代无官妓之制,中叶前后,更不许京官押妓,犯夜之禁极严,于是
一种具有自然趋势的少数人的习癖进而为一种风气,以至于一种制度,在当时称为“私寓”制度。私寓开始的年代,我们不详,但它的收场,我们是知道的,清末北京伶界有一个开明分子叫田际云,艺名想九霄,他“以私寓制度,为伶界奇耻,欲上书废止之(宣统三年),呈未上而被有力者阻挠;御史某受贿,诬彼以暗通革命党,编演新剧,辱骂官僚,下诸狱者百日。民国成立,彼以贯彻初衷故,请愿禁止私寓,终致成功”。(鹿原学人《京剧二百年史》260—261页。)
关于相公的风气或私寓制度的内容,我们不预备细说,既成制度,其为倾靡一时,已经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作者以前因研究伶人的血缘的关系,箧中曾经收集到不少关于伶人的汇传的文献,都属于这时期以内的。伶人的所以会有人替他做传,又因类归纳,分格品题,而成汇传,这其间除了艺术的欣赏而外,必有弦外之音,而此弦外之音无他,就是同性恋的倾向。如今不妨把此种倾向比较显著。比较“顾名”即可“思义”的若干书目列后:
| 作者 | 书名 | 写作或梓行年份 |
| 安乐山樵《吴太初》 | 燕兰小谱 | 乾隆末年 |
| 黄叶山房主人 | 瑞灵录 | 嘉庆九年 |
| 众香主人 | 众香国 | 嘉庆十二年 |
| 杨懋建 | 长安看花记 | 嘉庆末年 |
| 播花居士 | 燕台集艳二十四花品 | 道光三年 |
| 杨懋建 | 辛壬癸甲录 | 道光初年 |
| 同上 | 丁年玉笋志 | 道光中 |
| 同上 | 梦华琐簿 | 道光二十二年 |
| 四不头陀 | 县波 | 咸丰八年 |
| 寄斋寄生 | 燕台花史 | 咸丰九年 |
| 余不钓徒 | 明僮小录 | 同治初年 |
| 殿春生 | 明僮续录 | 同治六年 |
| 小游仙客 | 菊部群英 | 同治十二年 |
| 沅浦痴渔 | 撷草小录 | 光绪二年 |
| 缺名 | 鞠台集秀录 | 光绪末 |
这十多种作品的“捧角”的意味都很重。第一,从书名上可以看出来,有的竟等于开“花榜”,好像唐宋以来对待妓女的故事一样(明代最甚,见《续说郛》及李渔笠翁的剧本《慎鸾交》)。第二,从作者的假名上可以看到,书名里既大都有“花”和“香”一类的字样,作者的名字自然不得不有樵采、渔钓、摘撷一类的字样。而《众香国》一书的作者自称为“众香主人”,虽说一厢情愿,亦是情见乎词,其为有热烈的同性恋倾向的人,是最为明显的。
一种风气的造成,因素虽多,物以类聚和处领袖地位者的榜样究属是最重要的两个。即如上文提到的毕秋帆,因为有了一个“状元夫人”,据说他的幕僚也大都有一些“男风”的癖习。钱泳梅溪的《履园丛话》是清人笔记里比较很切实的一种,中间(卷二十二)有《打兔子》一则说:“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幕中宾客,大半有断袖之癣: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协,欢情亦畅。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侍候。’或问:‘何为?’曰:‘将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满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后先生移镇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语。余(钱氏自称)适在座中,正色谓先生曰:‘不可打也。’问:‘何故’?曰:‘此处本是梁教王兔园!’先生复大笑。“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才敷差遭,也正见同性恋者数量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