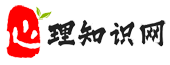就欧洲的民众而论,这种不欢迎国家的干涉的倾向是一向有的;他们往往让时光的过去和子女的出生来坐实这种性的关系。此种倾向并且早就在无数的农村社会里形成种种公认的风俗习惯,一面既不受外界潮流的激荡,一面也不受神学的基督教见解的制裁。但这还是比较过了时的话,若就近代而论,则此种倾向最称发达的阶级倒不是一般闭塞的平民,在他们中间,事实上已经不大存在,而是一些进步的知识阶级。马埃尔教授(BrunoMeyer)以为近代的性交,举行在合法的婚姻以外的,总要远在半数以上①。这话真无可非难,越是有知识,越是进步与繁荣的社会里面,此种不受法律的羁绊的倾向越是来得显著。所以就世界的大势而言,一般人的常识已经根据了理想的道德家所指示的方向,逐渐的在那里转变,慢慢形成一种实际的道德。
近代有许多婚姻是自动的不生子女的。这种婚姻更可以示人以自由结合的种种便利,于是风气所趋,诚有如巴孙士夫人(Mrs.parsons)所云,它已经变做“一种婚姻的进步的替代物”②。正式结婚的年龄的提高也是在一条路上的。它不但暗示自由结合的增加,并且告诉我们婚姻以外的性关系的各种方式,不论其为正常的或反常的,也都在那里孳长。例如在英伦与威尔
①见瑟南古所作《恋爱论》(Senancourt,Del’Amour).第二册,第233页。《英国的离婚问题》(TheQuestionofEnglishDivorce)的著者“某君”以为英国的淫风虽甚,而舆论不加苛责,原因就在高婚法律古板得大没有道理。
①见马氏所作《积极性改革论的管见》(EtwasvonPositiverSexua1reform)一文,载1908年十一月号的《性的问题》(SexualProb1eme)中。
②见夫人所作《家庭》(TheFamily)一书,第351页。夫人以为若此种结合,对于人格的发展发生阻碍,那未,也未始不是一种社会的恶事。此见甚是。
士,在1906年一年里,男子的平均婚年是28.6,女子的是26.4,而一千个男子中间还没有成年③的只有43人,女子也只有146人,也可见加入正式婚姻者的一般年龄的高大了。就1906年以前约四十年间的变迁而论,男子的平均婚年已经展迟了八个月光景,女子的还不止此。此种倾向,在大城市里也比在乡村里要来得显著,例如在伦敦,因为在城市里婚姻以外的性结合的机会与可能性,要来得大。
要是我们把目前的平均婚年当作一种富有代表性的东西,以为就大体而论,它也就是一般的人口初次发生性结合的年龄,那就未免大迟了。德国的一位神经学界的领袖,巴埃尔(Beyer)发见迟婚与早婚一样的有许多弊病,以为就温带的人口而论,女子最相宜的婚年是二十一,男子是二十五。
但是,在恶劣的经济状况与死板的婚姻法律之下,早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穷苦人家,它便是赤贫的一种表示。越是穷苦,越是结婚得早;他们觉得反正再穷也穷不到那里去①。但无论如何,穷人早婚总是一件不幸的事。霍华德协会(HowardAssocia-tion)的干事兼警厅的牧师、霍姆斯(ThomasHolmes)说:“许多好心肠的人劝青年男女早早结婚,免得发生他们所称的‘丑事’。我认为这是绝对的要不得的,它所作的孽要比它所能防止的更大更多”②。
早婚也是娼妓与离婚的一个极普通的原因。早婚的女子流为妓女的,多至不可胜数,有的名义上虽还是人家的妻子,实际上却在卖淫。至于和离婚的关系,则可以就离婚的统计推算出来。例如在英伦,上文不是说每一千个结婚的女子中间,不成年的只有146人么?但是在离婚的统计里,每一千个女子里,不成年的却有280。此种多寡悬殊的情形其实还不止此,要知道惟有小康和富裕的人家才可以享受离婚的艳福,而此种人家的结婚年龄总要比一般人口的高得多。这样一比,早婚与离婚的关系便越发显然了。很久以前,大诗人弥尔顿(Milton)说,少不更事是婚姻生活所由触礁的一个原因(弥氏自己在明白这一点教训以前,是付过代价的)。他在文章里说:“那些生活越是放浪的人,一旦正式结婚,越是能够成功,他们婚前的惹草拈花朝秦暮楚的行为,多了次,便无异添一次离婚的经验,经验便教训了他们”③。
克拉泊登女士(ClappertOn),就受高等教育的阶级而论,主张很早的早婚,以为就在学生时代,也不妨,认为婚姻生活和学业不难并行共进①。爱伦·凯也提倡早婚。但她也很聪明的添上一种附带的主张,就是,离婚也得方便。这是很对的,有了这唯一的附带的条件,早婚对于一般人才有可取之处。男女青年——除非具有很质朴和稳定的品性——大都不能预料他们自己的发育的途径和前途最强烈的需要,对于一个异性的人的性质与品格,也不能有准确的估量。在这种情形之下缔结的婚姻,结果虽不至名实两亡,也不免有名无实。在结婚的第二天,便向法庭要求分居或离异的女于,也就不乏其人。
③指满21岁,男女一律,比中国法定的成年迟一年。
①瑞盎医师(Dr.MichaelRyan)在他的《婚姻哲学》(PhilosophyofMarriage,1837年,第58—72)里,
搜罗了不少的有趣的材料,以示爱尔兰人所以早婚的理由。
②见和记者的谈话,1906年9月8日的《每日史纪》(DailyChronic1e)。
③这一番话不过是姑且引来,以示婚姻太早的危险,本身固不足为训。——译者
①见女士所作《科学淑世论》(ScientificMeliorism)第十七章。
欧洲社会里这种多少能够持久的自由结合,大都是只能当作一种“试验婚姻”看。虽有试验的意味,事实上却也是一种能适合一部分人心理的防卫行为。何以言防卫呢?一桩婚姻的成功,不论其为夫妇问的感情上的协调,或产生子女的能力,是事前不能预料的,既不能预料,便不妨先之以尝试,这是防卫的第一义。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对于离婚的条例是十分古板、十分陈旧的,凡是正式加入婚姻关系的人,往往进得去,出不来,即于婚后发见严重的错误,也往往不能用离异的方法来加以纠正。这种近乎陷阱式的婚姻,又谁愿贸然加入呢?这是防卫的第二义。所以这种试验婚姻,可以说是谨慎与远见的心理所要求出来的,远见既是一种和文明一起增加的东西,我们并且可以相信此种婚姻的频数和社会对它的态度,前途一定会有并行共进的发展。要叫它们不发展,前途唯一的方法是根本修改欧洲流行的婚姻法律,务使正式婚姻的解散,在经济上与手续上和自由结合的解散同样的方便。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法律的形成总要比舆论和习惯来得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