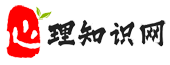①见女士所作《男子拳力杂论》(EinigesüberdieStarkeFaust)一文,载1905年出版的《女性论评》
(ZurKritikderWeiblichkeii)。
②探险家拉斯摩孙(Rasmussen)在他的那本《极北民族》(PeopleofthePOiarNorth)里,第56页上,描
写一对夫妇打架,起初打得非常凶险,彼此都把对方打倒过一次。“但不久以后,我再往里窥视的时候,
他们已经交颈熟睡,彼此还拥抱着咧”。
①可参看鲁杜维溪(A.MLudOvici)的作品:Lysistrata,(有中译本)wiman::AVindication;Man:AnIndictment.又刘英士译的《妇女解放新论》(MeYrickBooth,Womanandsociety),在这一层上也有发挥,此书现归
商务印书馆印行。——译者
②同注①所引霍氏书,第二册,第367页。德国女医师斯脱克(St(cker),在她的《恋爱与妇女》(Die
LiebeunddieFrauen),也极言个人责任是性道德的一大因素。
在道德生活的别的许多方面里,此种个人责任的观念,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是产生得比较很早的。惟有在性道德的一方面,我们到了最近才算取得了同样的观念,来做我们的准绳。性的势力原是一种不容易驾驭的势力,所以历来的社会,往往多方的造作种种很复杂的习惯的系统,来加以周密的防范,同时,对于社会分子的能否尊重此种习惯,也深致疑虑,不能不时刻提防。在此种形势之下,它当然不会容许个人的责任心有什么置嚎的余地。但经过许多世代以后,此种外铄的限制也自有它的极大的好处,它给我们以相当的准备,使可以享受自由之乐,而不至于受放纵之害。以前的神学家说,先世的律法是一个手拿戒尺的教师,可以引导后世皈依基督;近代的科学也这样说:先世不先受一种毒素的袭击,以至于受淘汰,后世便不能产生对此种毒素的抵抗力,而享受更丰满的生命;说法虽各有不同,而其精义则一。
一个民族要演进到了解个人责任的地步,是不易的,是很慢的,要是在一个神经组织还未臻相当复杂的程度的种族,此种观念怕就无从适当的发展。在性道德一方面,尤其是如此。在一个低级的文化和高级的文化发生接触的时候,这种观念的缺乏,便最容易看出来。宣教师到许多民族中间去传教,不由自主的把土著的严密道德制度给推翻了,也不由自主的把欧洲的自由的习惯给介绍了进去,但土著的民族对于这种自由是毫无准备的,毫无准备而作东施的效颦,结果真是糟不可言。这是已经屡见不鲜的事。中非洲的巴干达人(Baganda)原先组织很好,道德的程度也是很高的,详见兰姆金上校(ColonelLambkin)向政府的报告①,但後来就闹了一个乱七八糟。
在南太平洋的群岛上,情形也大致相同,文学家司蒂芬孙(R.L.Stevenson)的那本有趣的游记。《在南方诸海》(IntheSouthseas,第五章)里,说在白人光降以前,岛中上人大都是很贞洁的,对于青年男女的行为,也注意得很周密,现在是大不相同了。
就是在斐济(Fiji)岛的岛民,情形也不见佳妙。太平洋高等委托官(HighCommissionerofthePilcific)史丹摩勋爵(hordStan-more)是一个不耳食的评论家,他有一次说:传教的工作在岛上有“奇伟的成功”,所有的岛民至少在名义上没有一个不是教徒,岛民的生活与品格也已经改变不少,但贞操却受了打击了。有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斐济土著种族的状况时,也发见这一点,在他们的报告里也记了下来。费郄德先生(Mr.Fitchett)
评论这个报告的时候,说①:“委员会所根据的见证中间,有好几个说,岛上的道德的进步是像补缀的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的,教人见了觉得奇怪。例如他们说:多妻制的废除,对于女子未必完全有利。在斐济岛上,女子原是一个劳作的人,以前多妻制通行的时候,一个丈夫的供养,是四个妻子分担的事,所以责任轻,现在却要一个妻子独任其劳了。在基督教没有来到以前,女子的贞操,是用棍子来保障的;一个不忠贞的妻子,一个未结婚的母亲,一棍子就给打死,倒也干净。基督教却把这棍于的法律给取消了,它劝诱大家用道德的制裁,又用天堂地狱之说来警醒人家,但岛民的想像能力终究有限,天堂的好处,他们既见不着,地狱的痛苦也觉不到,于是实际的效力反而不及那根棍子,而岛上的贞操的标准便低得教人伤心了。”
我们得始终记住,原始民族的种种有组织的精神与物质的约束一经破
①《不列颠医学杂志》,(BritishMedicaIJourna1),1908年10月3日。
①1897年十月份的澳洲《过眼录的过眼录》(ReviewofReviewS)。
损、一经取消以後,贞操这样东西便越见得像惊涛骇浪中的不击之舟,动不动便有翻沉的危险。个人责任心的自动的制裁,价值虽大,虽属万不可少,终究不能把爱欲的火山爆发一般的力量,永远的丝毫不放松的扣住;这在文明大启的民族里犹且不可,何况别处呢?兴登说得好:“一个女子,无论她的道德的品质怎样圆满,意志怎样贞固,要‘好’的心愿怎样坚强、也无论宗教的势力与风俗的制裁怎样普遍周密,她的所谓德操是不一定能够保持的。假定有一个男子,能够打动她的那种绝对的笃爱的情绪,这情绪就可以把上文的种种一扫而光。社会不明此理,而完全想把这些做它自己所由树立的基础,它就无异选择了无可避免的未来的混乱。基础不改,那混乱局面也就不改”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