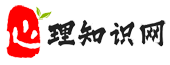不过我们这样推崇恋爱,我们还没能把它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恋爱实在还有比此更大的价值。所谓“情欲的班头盟主”,也许只不过是一种放大的唯我主义,一种牵涉到两个人的唯我主义,就是法国人所说的égOismeàdeux。比起单纯的唯我主义尽管大一点,终究并不见得更崇高,更雍容华贵。照我们在上文所了解的,恋爱也可以说是一个生发力量的源泉,而在恋爱中的两个男女是生发这种力量的机构,如此,则假若双方所发出的力量都完全消磨在彼此的身上,这不是白白地耗费了么?恋爱原是一种可以提高生命价值的很华贵的东西,但若恋爱的授受只限于两人之间,那范围就不免过于狭小,在有志的人,在想提高生活水准的人,就觉得它不配做生活的中心理想了,这话罗素也曾说过,我以为是很对的。②于两人之外,恋爱一定要有更远大的目的,要照顾到两人以外的世界,要想象到数十年生命以后的未来,要超脱到现实以外的理想的境界,也许这理想永无完全实现的一日,但我们笃信,爱的力量加一分,这理想的现实化也就近一分。“一定要把恋爱和这一类无穷极的远大目的联系起来,它才可以充分表现它可能有的最大的庄严与最深的意义。”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剩所谓恋爱的那一半由于外铄的基本条件了。这
①见马氏所著《经绝》(TheClimacteric)一书。
①见菲氏所著《性与恋爱生活》一书。
②霭氏这一点观察是很深刻的,如果在西洋比较范围小的家庭里犹不免有此种现象,中国式的大家庭的不
能没有此种现象是可想而知的了。在中国的大家庭里,青年人所受的痛苦总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咎到祖母或
母亲在经绝时期所表示的特殊心理。
外铄的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就在道学家也承认,他们对它的细节虽不免因道学的成见而存心忽略过去,但大体上也总是接受的。这条件就是上文提到过的“从恋爱的对象身上所取得的快乐的感觉”(joyinitsobject)。说到这里,我们也就说到了恋爱为什么是一种艺术了。
在以前,不很久以前,恋爱的艺术,在心理学与伦理学的书本里,是找不到一些地位的。只有在诗歌里,我们可以发见一些恋爱的艺术,而就在诗人,也大都承认,他们虽谈到这种艺术,却也认为这是一种不大合法而有干禁忌的艺术,所以谈尽管谈,只要许他谈,他就心满意足,但他并不觉得这是应当谈的或值得谈的。十五世纪以前,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许多关于恋爱艺术的诗词,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而这种诗,有的人以为真是合乎艺术的原则,而加以歌颂;有的人则以为是诲淫的,而加以诅咒。一直到近世的基督教化的欧美国家,大家的看法始终如此。一般的态度,总以为性爱至多是一种人生的责任,一种无可奈何的责任,因此,把它在众人面前提出来讨论,或在文艺里加以描绘,是不正当的、不冠冕的以至于不道德的。①有人说过,就近代而论,恋爱艺术的萌蘖,是到了十二世纪的法国才发见的,但其为一种艺术,却始终是不合法的,只能在暗中发展。
到了今日,情境才起了变化。把恋爱当做艺术的看法如今己渐渐得到一般人的公认。他们觉得这种看法终究是对的,并且道德学家与伦理学的接受与主张这种看法,倒也并不后人。他们承认,只是责任的观念,已经不足成为维持婚姻关系于永久的一种动力,我们诚能用艺术的方法,把恋爱的基础开拓出来,把夫妇间相慕与互爱的动力增多到不止一个,那也就等于把婚姻的基础更深一步地巩固起来,把婚姻的道德的地位进一步地稳定起来。②我们在这一节里并不预备专门讨论婚姻的道德,但这种道德的见地与要求我们是充分地承认的。
承认恋爱是一种艺术,其初期的一番尝试也还相当早,在近代文明开始之初,我们就有些端倪了。法国外科医学界先辈大师帕雷教夫妇在交接以前,应当有多量的性爱的戏耍(1ove-play),作为一个准备的功夫。更晚近的则有德人富尔布林格在他讨论婚姻的性卫生一书里,认为凡是做医师的人都应当有充分的学力和才识,可以对找他的人,讲解交接的方法与技术。再回到和性爱艺术的初期发展特别有关系的法国,1859年,医师居约发表了一本《实验恋爱编》(Bréviairedel’AmourExpérimenta1),把性爱艺术的要点极削切精审地介绍了一番;过了七十多年(1931),此书才有人译成英文,书名改称为《婚姻中恋爱者的一个仪注》(ARitualforMarriedLovers),仪注的说法很新颖可喜。说到这里,我们就追想到女子性冲动的
①曾经做过罗素(BertrandRussell)夫人的布莱克女士(MissBlack)主张过,女子在婚姻以后,最初十年或十五年作为生养与教育子女的时期,过此便是从事职业的时期。这一类妇女生活分期的主张可见是可以有生理与心理的根据的。(参看译者所作霭氏《性的道德》一文的译本的序言,第5页。)最近西洋有
人著一书名《事业前程在四十岁以后》(CareersafterForty)。译者尚未见其书,但就书题顾名思义,大约也是根据这种心理认识而写的。
②此与中国人从前的了解可以说完全相同,中国“八八六十四精绝”之说正相当于西洋六十三岁的大关口。
西洋人算年龄是算足的,所以西洋的六十三岁等于我们的六十四岁。人类真正的经验大抵是相同的,初无
分古今中外,特别是生理方面的经验,这也是很现成的一例了。
③见沃氏所著文《男性关口年龄的一些意外遭遇》;《不列颠医学杂志》,1923年1月9日。
种种特点,以及女子性生活中所时常发生的性能薄弱或性趣冷酷的现象。惟其女子的性能有这种种特点以及不健全的表示,恋爱的艺术才得到了发展的鼓励,而整个动物界中,何以求爱的现象大率有成为一种艺术的趋势,也就不待解释而自明了。
我们在上文已经说到,女子的性趣冷酷,可以产生家庭间的勃谿,妻子因此而受罪,丈夫因此而觖望,或终于不免于婚姻以外,别求发展。在这种例子里,其所缺乏的,或为性交的欲望,或为性交时的愉快,往往是二者均有不足;无论何种情形,都需要恋爱的艺术来加以补救。
性交接,包括初步的性戏耍在内,原是一个生物的活动;在这活动里,雌的所扮演的,正常的是一个比较被动的部分,而在文明的女子,这相对的被动的地位,不但受自然的驱遣,并且受习俗的限制,不免越发变本加厉起来。阳性刚而主动,阴性柔而被动,确乎是自然界的一大事实,阴阳刚柔的学说,只要不过于抹杀武断,是有它的价值的。这种二元的区别是极基本的,而男女两性在心理上的种种差异也就导源于此;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也是近代人士最容易忘怀的一个事实。④布赖恩说得好,两性之间,性的紧张状态,既相反而相成,则彼此在自己的身心上所引起的种种感觉与反应,也自不能一样;易于兴奋的阳具所产生的反应是急遽的推动、不断的活跃、具有侵占性的霸道的活动等等,而知觉锐敏的阴道所产生的反应是比较静待的容受、被动的驯服等等。换言之,我们在这里可以发见所谓“男性”和“女性”两者不同的精义。不过,布赖恩也曾经提示给我们看,①在我们到达这阳动阴静的阶段以前,即在求爱的较早的一段过程里,所谓动静的地位是多少有些对调的;即阳的反有几分柔顺驯服,而阴的反有几分主动与几分作威作福。:女子的性神经中枢,数目上既较多,分布上亦较散漫,因此,性冲动的驱遣、疏散与满足,往往容易找到许多比较不相干与意识界以下的途径,而同时,把性事物看做龌龊与把性行为看做罪孽的种种传统的观念,也容易在女子身上发生效力,从而教她把性的冲动抑制下去。也因此,自古以来,女子的性冲动,比起男子的来,也就容易被摈斥到意识的下层里去,容易从不相干与下意识的途径里找寻出路。弗洛伊德的学说的所以成功,就因为他能把握住这一层大有意义的事实。不过,女子虽有这种种无可否认的性的特点,我们却不能根据它们而怀疑到女子本来就有一种寂寞与冷酷的自然倾向。我们知道,在相当不违反自然的生活环境里,性趣冷酷的女子是不容易觅到的。即在文明社会的穷苦阶级里,说者都以为“老处女”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分的女仆是例外,她们的生活状态是很不自然的,像许多家畜一样);即此一端,虽不能证明女子的性能本质上并无缺陷,至少也可以暗示到这一点。不过就文明女子而论,情形就不同了。在自然、艺术、习俗、道德与宗教的协力的影响下,等到她经由婚姻而到达丈夫的手里对,她往往已经是一个将近徐娘半老的人(原文是成年期后半的人),已经不大适宜于性交接的行为,所以,除非做丈夫的人特别有些艺术上的准备与性情上的温存体贴,结果,床第之私,只足以引起她的痛苦、厌恶,或对她只是一种味同嚼蜡的反应罢了。
④见托氏所著《人类的睾丸》一书。
①本节所引书外,尚有二书可供参阅:
:《生殖的生理学》。
当然,在女子自身也容或有种种不健全的状态,有不能不干事先加以治疗或纠正的。早年自动恋或同性恋的癖习往往可以使女子对正常的性交发生厌恶,视为畏途,在性交之际,也确乎可以有许多困难。或许性器官本来不大正常,而多年的处女生活的恝置不问,又不免增加了这种不正常的程度,又或许有阴道口过度紧缩的状态(vaginismus)(。对这种例子,妇科医师的帮忙是不能少的,而一经诊治以后,自然的性的感觉也许很快而且很满意地发展起来,而性交之际,也不难达到亢进的境界。不过大体说来,要治疗妻子的性感缺乏,主要的责任通常总是在丈夫的身上。所可虑的是做丈夫的人不一定都有这种准备。我们很怕法国名小说家巴尔扎克(Balzac)一句很杀风景的话到如今还是太与事实相符,他说,在这件事上,做丈夫的人好比猩猩弹小提琴!小提琴始终不能应手成调,始终好像是“缺乏感觉”似的,但这也许不是小提琴的错误。这倒并不是说做丈夫的人是自觉地或故意地鲁莽从事。做丈夫的人,如果太没有知识,太被“为夫之道”的义务观念所驱策,大量的鲁莽行为当然是可以发生的。不过,做丈夫的人,一面固然外行,一面也未始不真心想体贴他的妻子。最可以伤心的是,就很大一部分实例而言,丈夫的所以外行,所以笨拙,是端为他是一位有道之士,一位有高尚理想的青年,当其未婚以前,他的生活曾经是玉洁冰清到一种程度,几乎不知道世上另外有种动物,叫做女子,姑且不论女子的本性与女子在身心方面的需要了。我们固然得承认,最美满的婚姻,最能白头偕老、始终贞固的婚姻,有时就是由这样的两个玉洁冰清的青年缔结而成;他俩在婚前婚后真能信守“不二色”的原则。但这种玉洁冰清的态度与行为可以比做一把两面是口子的刀,操刀的人用这边的口子来割,是有利的,若用那边,就是有害的,而就不少的例子而言,操刀的人往往用错了口子。所以一个在旧时宗教与道德观念下所培养出来的青年,在结婚以前越是“天真”,越是“纯洁”,一旦结婚以后,他会突然发现,这种“天真与纯洁”便是粉碎他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惟一的礁石,害了自己,又害了妻子。不过话得两面说,一个在结婚以前专以寻花问柳为能事的青年,比起这种“天真”的青年来,在准备上也是一样的不适当,寻花问柳的人失诸过于粗鲁轻率,不免以待妓女的方法来待妻子,“天真”的青年则失诸过于顾虑到妻子的“纯洁”,其不幸的方向虽大有不同,而其为不幸则一。我们得承认所谓丈夫的责任也往往并不容易尽到。近代晚婚的倾向,特别是在女子方面,更教做丈夫的不容易尽到这种责任。在近代的文明状况下,女子在结婚以前,总有不少的年份是过着一种我们不能不假定为比较贞洁的生活,我们也不能不假定,在这许多年份以内,她的性的活力,象电一般地发出来以后,总得有些去路,有些消耗的途径。而在寻觅去路之际,她总已养成种种比较牢不可破的习惯和陷入种种比较摆脱不开的窠臼;她的整个神经系统总已受过一番有型的范畴,并多少已很有几分硬化。就在性的体质方面,她的器官也已经失掉几分原有的可塑性,以致对于自然功能的要求,不容易作正常的反应。迟婚的女子第一次分娩,往往有许多困难,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但迟婚者的初次性交也有许多困难,并且这两类困难是彼此并行而同出一源的,却还不大有人充分了解。很多人以为青年期的前半不适宜于结婚与发生性交的关系,以为此时期内的性交,
(w.GaIlichan):《女子的危机年龄》。
①关于恋爱的艺术,霭氏别有详细的讨论,见《研究录》第六辑第十一章和《恋爱与德操小言集》。
对女子无异是强力奸污;这种见解实在是一个错误。实则事理恰好与此相反,一切事实都能证明一个青年期内的少年女子,比起一个成年的女子来,对于初次的性交经验,要容易领略得多。要知初次性交经验的必须像目前的那般展缓,所有的理由只有文明社会的传统观念做依据而并无生物事实的依据。在动物进化的过程里,发育成熟的期限,固然有越来越展缓的趋势,这种趋势当然也有它的意义,但我们应当知道,进化过程中所展缓的是春机发陈的年龄,而不是春机发陈以后的初次的性交关系,而人类的春机发陈,已经是够迟缓的了。文明社会的种种要求固然迫使我们把性交行为的开始越往后推越好,但若我们顺受这种逼迫,结果便是我们无可避免地要自寻许多烦恼。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要解除这种烦恼,便更有乞灵于性爱的艺术的必要。
总之,我们要对男子的性生活加以调节,我们必须就女子方面同时加以考虑,这是显而易见的一种道理。更显然而同时却又不得不加申说的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女子的性爱方面的心理生活,我们也必须兼顾到男子的方面。
女子的性生活大部分受男子性生活的限制和规定,这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而必须了解的理由也不止一个。这些理由我们在上文大致都已经提到过,不过性爱的艺术在性心理学方面既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不妨再提出来讨论一下。第一点,我们要再度提到阳动阴静、阳施阴受的道理。常有人说,并且也说得不无几分理由,在性的题目上女子实在处于一个优越与支配的地位,而男子不过是她手里的一个玩物罢了。话虽如此,基本的事实却并不如此。我们充其量说,就我们和大多数的生物所隶属的高等动物界而言,阳性总是比较主动的,而阴性总是比较被动的。就解剖学方面而言,以至于就生理学方面而言,阳性是施与者,而阴性是接受者。而心理方面的关系也自不能不反映出这种基本的区别来,尽管在种种特殊的情形下,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上,这阳施阴受的自然原则自然规范,可以有些例外,但大体上是不受影响的。
第二点,既不论自然的雌雄的关系,我们有史以来,以至于有事迹可据的史前时代以来,一切男女关系的传统观念也建筑在这一大原则上。我们承认,在性关系的树立上,男子占的是一个优越与支配的地位;我们更从而假定,在这方面、女子主要的功能,以至于惟一的功能,是生男育女,任何性爱的表示,要有的话,多少是属于不合法不冠冕的一些串戏性质,没有正规的地位的。我们的若干社会制度也就建立在这条原则与这种假定上,演变出来,建立起来:即如婚姻制度,我们一面承认家庭中丈夫有法定的家主的地位,而妻子则不负法律的责任,即妻子对丈夫负责,而不对社会负责;一面又于婚姻以外,承认娼妓的存在,以为只有男子有此需要,而女子则否。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过火的,不全合事理的;幸而近代的社会舆论与国家法律已在这方面有些变迁。不过我们也应当知道,古代传下来的制度,尤其是这种制度在我们身上所已养成的种种情绪与见解,要加以改正,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决非朝夕之间可以收效。我们目前正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之中,即在过渡的时代里,凡百的变迁要比较快,我们依然不免很深刻地受到已往的影响。
还有根值得考虑的一点,这一点和上文的两点也有些渊源,不过和女子方面的心理生活的领域更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羞涩的心理。羞涩的心理有两部分:一部分可以叫做自然的羞涩,那多少是和其他的高等动物共通的;第二部分是人为的羞涩,那一半就建筑在社会习尚上面,而是不难加以修改
的。世间也有怕羞的男子,但羞涩终究是女子的一种特殊的品性。这其间详细的情形以及种种例外的事实,不在本节的讨论范围以内(参看上文第二章第三节末段),不能具论。不过就大体而言,羞涩的品性是女子心理的一大事实,不容怀疑的,它和一般阴性动物在性活动之际所表示的柔顺驯服的性格有极密切的先夭关系,而和社会的习俗又有不少的后天关系,并且此种先天的关系,因后天的关系而越发见得牢不可破。(不过上文说过,后天的关系是可以修改的,至于可以修改到什么程度,晚近的裸体运动很可以证明,裸体运动的会社近来一天多似一天,而男女社员可以完全以裸体相见而不露丝毫的窘态。)就一般的情形而言,这种后天关系的修改是不大容易的,传统的种种习惯,近来虽已发生不少变迁,但显著的效果也还有限。不但有限,并且暂时还有一种不良的趋势,就是在女子的意识上,引起一种不和谐的局面。意识包括两方面,一是体内的感觉,二是身外的表现;今日的女子对于自身内在的性的感觉欲望,已经有自由认识的权利,但要在身外表示这些感觉与欲望,她就往往没有这种自由了。结果是,现代的女子之中,十有七八知道她们要些什么,但同时也知道,如果她们把这种需要老实地说出来,势必至于教对方的男子发生误会,以至今男子作呕;因而把男子拒于千里之外。这样,我们的话就又得说回来;我们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开导男子,让男子了解女子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男子的身上。
就是这两三点的讨论可以足够提示给我们看,我们目前所认识的女子应有的性生活的领域,实在有两个,而这两个是彼此冲突的。第一个是,女子性生活的理想是极古老的,可以说和我们的文明同样的古老,这理想说,女子的性生活应以母道为中心事实,这中心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这理想又说,这中心事实以外,其余的性生活的领域大体上全应由男子执掌;女子除了为成全她的母道而外,是没有性冲动的,即使有,也是等于零的;因此,女子的天性是单婚的、一夫一妻的、从一而终的,而男子那方面,既无需困守家庭,又少子女养育之累,心理品性的变异范围便比较大,婚姻的倾向也就很自然地会走上多妻的路。又因此,女子的性的问题是单纯的、显而易见的,而男子却要复杂得多。这样一个女子性领域的观念,我们几乎可以武断地说,是远自古典时代以迄最晚近的现代大家所认为自然的、健全的、而不容易有异议的,至于与确切的事实是否相符,那显然是别一问题。不到一百年前,英国的外科医师阿克登(Acton)写了一本关于性的问题的书,他说,我们若认定女子也有性的感觉,那是一种“含血喷人”的恶意行为,而这本书便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前在性的题目上惟一的标准作品与权威作品!②在同一个时期里,在另一本标准的医书上,我们发见写着,只有“淫荡的妇女”在和她们的丈夫交接的时候,会因愉快而做出姿态上的表示来!而这一类荒谬的话,居然受一般人的公认。
到了今日,另一个女子性生活领域的观念正在发展。这个新观念,我们
②这话是再对没有的。译者以前在别处讨论过,前代中国人很大一部分的殉国或杀身成仁的行为是由于忠君爱国的情绪,也是一种爱,成仁的仁。不用说,也是根源于爱的情绪;爱国而至于殉身,不能不说是尽
了自我牺牲的能事。然此类成仁的人,其动机之中,也多少总有一些保全名节的观念,读书人之于名节,
好比寻常人之于身家财产,都是自我的一部分;名节何以要保全?因为它是名教纲常的一部分,固然有保
全的价值,同时也正因为它是我的名节,所以更有保全的必要。为保全名节而牺牲自我,其问同样可以有
自我满足的成分存在;不过和保全身家性命的自我满足相比,其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了。
也许得承认是比较健全的,一则因为它和两性价值均衡的观念互相呼应,③再则因为它和自然的事实更相吻合。在今日的情形下,就在性生活的领域以外,我们对男女两性的区别的看法,也不像以前那般斩钉截铁。我们承认两性之间有极基本的差异,并且就其细节而言,也真是千头万绪,无法清算,但这些差异只是一些很微妙与隐约的差异。若就其大体而言,则男女既同为人类,便自有其共有的通性,换言之,人性终究是一个,而不是两个。
男女同样有做人的通性,也同样有此通性的种种变异的倾向。两性之间,变异的趋向容有不同,但始终不至于影响通性的完整。我们已经再三提到过男子天性多婚与女子天性单婚的那句老生常谈,这句老生常谈究有几分道理,几分真假,我们也已经加以讨论。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就男女自然的区别而论,一样是性交接的行为,其对女子所发生的影响与责任,在分量上,比对男子的要重得不知多少,因此,女子在选择配偶之际,比起男子来,就出乎天性要审慎得多,迟缓得多。这个区别是自有高等动物以来便已很彰明较著的。但也尽有例外。世间也很有一部分少数的女子,一方面对母道完全不感兴趣,而另一方面则和寻常的男子一样,可以随时随地和不同的许多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一般女子喜新厌旧的心理,好动善移与去常就变的心理,也大体上和男子没有区别,因此,假定有所谓三角恋爱事件发生的时候,以一女应付二男,比起一男应付二女来,不但一样的擅长,有时则更见得八面玲珑,绰有余裕。⑤总之,把男女看做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彼此之间有一道极深的鸿沟,极坚厚的铜墙铁壁,这虽属向来的习惯而至今还没能完全改正,可见是没有多大理由的。女子像她的兄弟一样,也是父亲生出来的,因此,尽管男性与女性之间,有无数的细节上的差异,彼此所遗传到的总是人类的基本的通性。男女的所以隔阂,以至于所以成为一种对峙与对抗的局面,由于自然的差异者少,而由于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不同的观念者多。我们在今日的过渡时代里,正目击着这种不同的观念或不同的理想所引起的明争暗斗。
我们看了上文的讨论,便知道我们对于女子性生活的实际状况的了解,为什么必须要寻找比较大批的精审而有统计数字的资料?女子一般的性生活状况如何?正常的女子如何?不同阶级或团体的女子又如何?比起男子来又如何?这一类问题的答复,非有精审与统计的资料不办。只是笼统武断的叙述,尽管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尽管描绘得活龙活现,是没有用的。精神分析家和其他作家所能供给的往往就是这一类的叙述,并且这种叙述又不免被学说的成见所支配,多少总有几分穿凿附会,即或不然,其所有的根据又不免为少数特殊的男女例子的经验,实际上不能做一般结论的张本。幸而这些如今都已渐成过去的事物,而事实上我们也无需再借重它们。客观的调查与统计的资料原是最近才有的事,但幸而没有再晚几年,否则我们今天便无法利用。我们在上文已经屡次引到过戴维斯、狄更生、汉密尔顿三位男女医师
③可参阅译者所著的《冯小青》。
④中国文字在这一点上很可以和这段讨论相互印证。说文中有“厶”字(今私字从此,且己取厶字而代之),
八厶即为公,八就是分,把厶分配出去,或推广开去,就成为公,故公中不能完全没有厶的成分,而公的
观念根本需从厶发展出来。男女的关系如此,一般人我的关系也复如此。这看法是最合理而健全的,有此
看法,则西洋社会思想中“群己权界”一类的困难问题便根本不会发生。
⑤雁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富有人本思想与浸淫于拟人论的中国文学家也早就观察到此。
的结论,我们如今还要借重他们。上文说,在性生活的领域里,女子的被动性似乎比较大,这一点是不是就暗示在生理方面的性要求和心理方面的性情绪,男女之间也有根本的差别呢?为测验这一点,我们倒有一个方便的尺度,那就是性冲动的自动恋的表现,在男女之间,在频数上有什么相对的差异。汉密尔顿、戴维斯和狄更生,在这一点上,都有过一番周详的探讨。为什么自动恋的表现与其频数可以做尺度呢?大凡有到自动恋的表现,无论表现的人是男是女,我们便有理由可以推论,说背后总有一个主动的性欲在;固然,性欲之来,是可以抑制而不是非表现不可的,但只要有些表现的事实发生,我们一样的可以作此推论。三位医师所供给的数字当然并不一样,因为三家的探讨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而他们在征求答案的时候,被征的人有答不答的自由,并没有必须照答的义务,因此,有的问题就被跳过。据说这种跳过的脾气,女子要比男子为大。如果女子真有这种脾气,那么,凡是坦率承认有过主动的自动恋的答复,当然是特别有意义的,而这种答复越多,那意义便越大,这是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加以说明过的。据狄更生的发见,通常属于各种不同阶级的女子,经验到有充分力量的性欲要求的有70%,足以使她们时常采用自动恋或手淫的方法,作为解欲的途径。戴维斯女医师,在1000个未婚的大学女生中,发见65%的答复(跳过未答者不计)承认她们有过手淫的活动,其中有一半更承认在作答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放弃这种习惯,而在这些没有放弃手淫习惯的女子中,健康属于“最优等或优等的”,比起已经放弃或从无手淫习惯的女子来,人数要来得多;这大概是有意义的,因为性冲动的健旺就是一般身心健旺的一种表示。汉密尔顿所研究的都是一些地位与才干在中等以上的已婚女子,而这些中间,只有26%郑重声明从小没有手淫过;同时,汉氏又观察到一种倾向(这我自己在许多年前便观察到过),就是,女子手淫习惯的开始,总在童年过去以后,而一般开始的年龄又大率比男子要晚,例如,在满25岁以后才开始手淫的,在男子中只有1%,而女子要占到6%。此外,汉氏的观察里还有许多有趣的发见。手淫的习惯,有的是由别人诱引的,有的是自动发见的,但两者相较,自动发见的例子,无论男女,要多得多。通常以为此种习惯的开始大率由于旁人的诱惑,由此可见是不确的了。
还有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在结婚以后,放弃手淫习惯的,男子虽只有17%,而女子则有到42%,但在结婚以后,依然手淫并且“屡屡”为之的,女子的数目差不多和男子相等,并且在婚后依然手淫的全部的女子中,也几乎占到半数;换言之,婚后依然“屡屡”手淫的女子要比男子为多,而偶一为之的,则男子比女子要多得多。这一层似乎告诉我们,已婚的男子手淫,大部分是因为旅行在外,或因其他外来的原因,而已婚的女子手淫,则总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床第生活的不能满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认为手淫的习惯对i身心的健康有不良影响的男子,要比女子多得多。
三位作家中,只有汉密尔顿对于夫妇双方所能经验到的床第生活的相对满意,有过一番直接的探讨,因为他的研究对象里是夫妇都有的,并且数目相等,地位相当,可以比较,而调查的方法又复完全一样。他把满意与否的程度分成14等,他把各等的程度整理而列成表格以后,发见能够达到第7等的高度满意境界的,丈夫中有51%,而妻子中只有45%。换言之,在妻
⑥伊奥尼亚为古希腊的一部分,由若干岛屿组成,雅典便是这一部分的中心都市。
子方面,就全体而言,对于婚姻的失望,要比丈夫更见得严重。戴维斯女医师虽未直接比较这一点,但也能从旁加以坐实,因为她所研究的妻子在答案里提到对于婚姻表示满意的,以她们的丈夫为多,而她们自己则较少。我自己对英美两国婚姻的观察,虽没有汉、戴两家的精审,也很可以和他们先后呼应。总之,夫妇双方所表示的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差别虽未必大,但是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来。
女子并没有什么特殊而与男子截然不同的性心理,这一层是越来越明显的。说女子有特殊的性心理,那是修士和禁欲主义者所想出来的观念,不过既成一种观念,也就流行了很久,到现在才渐渐被打消。不同的地方是有的,而且永远不会没有。男女之间,只要结构上与生理上有一天不同,心理上也就一天不会一样。不过在心理方面的种种差别,终究不是实质上的差别。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就基本的要素而言,男女的性的成分是一样的,来源也只有一个,而西洋一部分人的旧观念,认为这样便不免“有损女子的庄严”,那是捕风捉影的看法,要不得的。
我们也看到,在性的境遇里,女子吃的亏大抵要比男子为大,这其间主要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以前的知识太不够,而传统的成见太深。虽则一部分的旧观念认为婚姻制度是男子为了女子的幸福而创立的,但事实上在这个制度里,女子受的罪要比男子为大,女子所获得的满意要比男子为少,不但一般的印象如此,更精审的妇科医学的证据也指着这样一个结论。例如,在研究到的1000个已婚女子中,狄更生发见175个有“性感不快”(dyspareunia)的现象,就是在性交的时候,多少会感到痛楚和不舒适,而对另外120个女子,在性交之际总表示几分性趣冷淡或性能缺乏,而这些在事实上也就和性感不快没有区别。而就丈夫方面而言,这两种情形是可以说完全不存在的(惟一可以对比的现象,所谓性能痿缩,即阳痿,那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实在不宜相提并论)。总之,即就这一端而言,女子所处的地位是有比较重大的不利的。
女子的这种不利,究属有几分是天生的,又有几分是后天环境所酝酿出来、因而还可以控制补救的呢?大抵两种成分都有。换言之,要在性交关系上取得充分的身心两方面的调适或位育,就在正常的形势下,女子本来比较难,而男子比较易。那当然是一个自然的不利,但也多少可以用自然的方法来加以纠正。目前我们的问题是,不幸得很,这种局部基于自然的不利,在人类以前的历史里虽多少也感到过,但似乎从没有像近代的这般厉害。戴维斯女医师,在转述她所研究的各个已婚女子的经验时,提到有一位曾经很惨痛地问道:“为什么做丈夫的在这方面不多受一点教育呢?”至于这些经验是什么,我们很可以从已婚女子的一部分答复里领悟得到。戴医师问大家对婚姻第一夕的反应如何,她们简短地答复:“啼笑皆非”、“可怜可笑”、“十分诧异”、“满腔惶惑”、“一场失望”、“惊骇万状”、“愤恨交并”、“听天由命”、“手足无措”、“呆若木鸡”等等;同时有173个例子好像世故很深似的“承认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作这一类答复的女子大部分是在结婚前,对婚姻的意义,对婚姻的葫芦里究竟有些什么药,几乎全不了解,事前既全无准备,临事自不免发生这一类惊惶失措的反应了。这样,我们的讨论貌似到了尽头,实际上却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
在以前,女子和她的性的情境之间,可以说是有一种适应的,至少,一种浮面上的适应并不缺乏,因为女子在结婚以前,对于和当时当地的生活应
该发生一些什么密切的关系,多少总有几分训练,也可以说这种比较不能不密切的关系自会不断地给她一些训练,事前让她知道,让她预料,婚姻的葫芦里大概有些什么药,临事她也可以发见预料得大致不错。⑦到了更近的时代,她们不是全无训练,便是训练得牛头不对马嘴,训练的结果,也可以教她在事前预料婚姻的葫芦里有些什么药,但临事她会发见压根儿不是这么一回事。换言之,近代以来,妇女的身分地位,妇女的每一个活动的园地,都静悄悄地经历着一番革命,其结果虽对性冲动井无直接的影响,而一种间接的、并不存心的、牵牵扯扯的影响,却到处皆是,四方八面都是。而同时,在男子的地位与活动方面,却并没有发生可以对比的革命,今日的男子还是五六十年前和七八十年前的男子。结果当然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失其适应的局面。妇女运动或妇女革命的种种效果,我们既无法加以打消,也不想加以打消,那么要修正目前已失其适应的性的局面,那责任的大部分就不得不由男子担当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丈夫来接待一个新的妻子。
生命的一切都是艺术,这话我以前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不过也有一些人不承认这句话。我以为这些人是误会了,他们把艺术和审美的感受力混做一回事,实际上却是两回事。一切创作,一切行为,都有艺术的性质,这不但以人类的自觉活动力然,一切自然界的不自觉的活动也可以说多少有些艺术的意味。说生命是艺术,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要不是因为时常有人作为矫情的反面论调或口头上虽承认而行动上却全不理会,我们也无需把它特别提出来。就现状而论,说不定也正因为这种矫情与言行不相呼应的人太多,我们忍不住要说,要是人生是艺术的话,那大部分不是美好的艺术,而是丑陋的艺术。
我们说人生大部分是丑陋的艺术,指的是一般的人生,但若就性爱的人生领域而论,我们似乎更忍不住要说这样一句话。我们常听见说,两性之间,真正更能在自然界表示或流露艺术的冲动的是阳性,而不是阴性,这话是不错的,许许多多动物界的物类确乎是如此(我们只需想到鸟类,就明白了),但若就在性爱领域以内的近代男子而论,就汉密尔顿、戴维斯、狄更生三位医师所和盘托出的种种事实而论,这样一个总括的结论,就很不容易达到了。这是很不幸的一个局面,因为恋爱这个现象,若当作性关系的精神的方面看,实际上等于生命,就是生命,至少是生命的姿态,要是没有它,至少就我们目前的立场而言,生命就要消歇。时至今日,我们对恋爱的艺术所以受人责备、忽略以至蔑视的种种原因,已经看得很清楚,并且可以很冷静地把它们列举出来,例如,宗教的、道德的、精神的、审美的等等。而这些原因的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根据,即基于成见者多,而基于事理者少,我们如今也看得很明白。这样一番认识,一种看法,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后要改进恋爱的艺术,这种看法是个必须的条件。我们也知道这种看法在目前已渐渐发生影响,即使与真正的事实与学理未必完全相符,但终究是个进步。有的人甚至根据这种新的看法,从而作为矫在过正的主张,就是,想把性的活动完全看作一种寻常日用的活动,一种尽人必须例行的公事,好比穿衣吃饭一般,或一种随时乘兴的娱乐,好比跳舞与打球一般,事前既不需广事张罗,临时
⑦这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特里斯坦的叔父,是康沃尔国(Cornwall,今英国西南部)的国王,名字叫做
马克(Mark);他衔叔父之命到爱尔兰迎娶新后叫依索尔德(lsoldetheBeautiful),在回程中,他和这位
新后共饮了一种药水,遂至彼此相爱,固结不解,后来终于被马克刺死。
也毋庸多加思索;他们认为只要采用这样一个看法,一切性活动所引起的问题便根本可以不致发生,更无论解决之烦了。这样一个主张,虽属矫在过正,也和以前的有些不同,就是,以前的人若有这种主张,往往是出于一时的意气,而今日的人作此主张,则大有相当的理论做依据。不过这种主张,终究是不健全的。英国的文学家与批评家赫看黎(AldousHuxley)对当代的生活风尚是有很深刻的观察与评论的一个人,他根据诗人彭斯(RobertBurns)的见地,曾经说过一句很真实的话:“冷漠而没有热情的放纵行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而恋爱这样东西,假如可以随便发生的话,结果一定是冷漠而没有热情的。”⑧还有一层我们不得不加以说明的,就是即使我们真把恋爱降低成为一种例行公事,或一种随兴消遣,我们对两性关系的协调问题,不但并不能解决,并且可以说很不相干。不久以前,我们把性结合看作一种义务,初不问其间有没有一些感情或浪漫的成分;那种情形固然是离开应有的健全状态很远,如今把性结合当作一种公事,一种娱乐,其为违反自然,其为与自然睽隔,事实上是同样远。》上自文明的人类,下至哺乳类以降的
⑧兼顾到精神方面的恋爱观,在中国也似乎发展得相当迟,除了重视同性恋一端而外,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和希腊的很有几分相象。我们现在用的恋爱二字,已经是后来的假借,恋爱二字并用而成词,更是近年来才流行。《说文》爱原作■,经传都以爱为之,而■字遂废。爱字最初训惠,训仁,训慕,并不专用于性爱的方面。《诗经·国风》中多男女相悦之词,但遍索的结果,只找到两个爱字和性爱有关,一是《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二是《将仲子》的三句相同的”岂敢爱之?”《国策》中的《齐策》“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一语中的爱显然是性爱之爱,但注里说,爱犹通也。孟子提到过:“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总之,爱当性爱用、在最初大概是很不普通的,偶一用到,也没有多大特殊的意义,更说不上意义中有多少精神的成分。《孝经正义》于“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一语下引沈宏的注释说:”亲至结心为爱。”结心二字的说法极好,但可惜所指并不是性爱,而是亲子之间的爱。恋字比起爱字来,似乎要更有性爱的意义。戀、孌、攣、■,古书上大率相通,从,从丝,有乱烦之意。《老子》说,不见可欲,则心不乱,戀字既从墩从心,可见应与性爱的情绪,最为相近。但在古时候也不见得如何通行。《易·小畜》,“有孚攣如”,子夏《传》作“戀如”,注谓“思也”;思字富有性爱的意味,说详下文。《诗经》上戀字皆作孌,如《泉水》的“孌彼诸姬”,《静女》的“静女其孌”,《猗嗟》的“猗嗟孌兮”,《车■》的“思孌季女逝兮”,《候人》与《甫田》的“婉兮孌兮”——大都用作形容词。而不用作动同,作“可爱”讲,而不作“爱”讲。我以为自形容词转用为动词,是后来的一个演变。好比婉字,最初显然是一个形容词,例如《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后来三国时阮璃为曹操致孙权书中,有“婉彼二人”(刘备张昭)语。即用作动词,即作爱字讲。
》的《国风》,不用说是最富有性爱情绪的一部文献,而恋爱的概念却始终不曾有过清切的表示,这是很
可以惊异的。不过《国风》有两个用得比较多的字,比爱字恋字要普通得多,我以为倒很有几分恋爱的意味。第一个是“怀”字,如《卷耳》的“嗟我怀人”及“维以下永怀”;《野有死麝》的“有女怀春,吉
士诱之”;《终风》的“愿言则怀”;《雄雉》的“我之怀矣,自治伊阻”;《载驰》的“女子善怀”;
《将仲子》的三句“仲可怀也”。第二个是“思”字。如《汉广》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桑中》
的三句“云谁之思?”;《伯兮》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与“愿言思伯,使我心海”;《褰裳》的“子
惠思我”与“子不我思”。《东门之》的“岂不尔思?子不我即”;《子衿》的“悠悠我思”;《出其东门》的“匪我思存聊乐我员”与“汇我思且聊可与娱”。《伯兮》与《出其东门》二诗里的几
个思字,最足以表示真正的恋爱的情绪。《伯兮》的主角是一个十分贞洁的女子,当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连修饰打扮的功夫都暂时废弃,而思慕之深,竟到一个“甘心疾首”与“心痗”的程度,所以我以为两句
“顾言思伯”里的思字决不只是代表寻常思虑的一个字。《出其东门》里的“思存”与“思且”,因为有
下文的“聊乐”与“聊娱”做对照,也是比较有特殊意义的,其意盖谓,东门外的游女虽则多如云,闉闍
动物界,性结合的行为,就一般正常的状态而论,事先总有几分犹豫,几分阻力,而要消除这种犹豫与阻力,而使结合的行为得以圆满的完成,其间必须有充分的热情与相当的艺术。如果我们想否认这个自然的基本生理事实,我们是一定要吃亏的,而所吃的亏还不限于一种方式。
至此我们就说到了恋爱的艺术在卫生学与治疗学上的重要,而不得不多加一番申说。在以前,这种申说是不可能的,并且即使说来,也没有人能了解。在以前,所谓恋爱的艺术是可以搁过一边的,可以一脚踢开的,因为妻子的性爱要求既向来无人过问,而丈夫的性爱要求很多人都认为可以暗地里在婚姻以外别求满足的途径。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夫妇双方的看法都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承认妻子和丈夫同样有性爱的权利;我们也渐渐指望着,所谓一夫一妻的制度会切实地经过一番修正,不再像已往及目前的那般有名无实,掩耳盗铃。因此,在今日,不讲求恋爱的艺术则已,否则势必最密切地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单婚制或一夫一姜制的培植,因为,婚姻之制,除了一夫一妻的方式以外,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无法维持的,而即在一夫一妻的方式下,婚姻生活的维持已经是够困难的了。
恋爱的艺术,就它的最细腻最不着痕迹的表现而论,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人格方面发生最亲切的协调的结果。不过就它的一般粗浅的程度而论,这艺术也未始不是寻常性的卫生的一个扩展,亦即未始不是医师的工作范围的一部分,换言之,如果寻常的婚姻生活产生困难的问题或遇到困难的情境时,是很有理由可以向医师领教的。目前一部分提倡性卫生的人还往往忽略这一点,但我相信这种忽略的态度终究是不能维持的,事实上也已经很快地正在那里发生变迁。我们到了现在,再也不能说,求爱与性交的知识是天授的,是天纵的,是良知良能的一部分,因而无需教导。好多年以前,英国名医师贝杰特就说过,至少在文明状态下,这种知识是要授受的。我们不妨补充说,就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里,这种授受的功夫其实是同样的需要,在这些民族里,男女青年到了相当年龄,便需举行很隆重的成人的仪式,而性交知识的训练便成为这种仪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人所不大注意而值得提出的一层,就是这些民族所处的环境既比较自然,对于性交前的种种准备步骤也往往能多所措意,而性交方式的繁变,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现象。这些参考之点都是很重要的。求爱或交接前的准备必须多占一些时间,因为,在生理方面,时间不多,则欲力的累积有所不足,上文很早就说过,所谓积欲的过程是要充分的时间的;而在心理方面,时间不多,则恋爱中精神方面的一些成分便无从充分的发展,而真正的婚姻生活便失所依凭,因而不能维持于久远。我们也必须承认,交接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的,不同的方式虽多,要不至于超越寻常人性的变异范围之外,换言之,它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并不是一些恶孽的根性的流露。我们更需承认,这些方式的变换也是必须的,因为对于有的人,或在有的时候,某一方式要比另一个更相宜,更有满足的能力。新婚夫妇,有时要经过好多年,才发见只有在某种情况下,采用某一方式,性交方才发生快感,或单就妻子方面而言,虽无快感,也至
外的游女虽则美如茶,在诗中的主人看去,只配做些寻常调情的对象,可以相互娱乐罢了,而说不到什么比较真正与深刻的性的情绪(按注疏的看法与此完全不同,孰是孰非.目前姑不深论,惟注疏一方面受了《诗序》的文词的限制,一方面又兔不了家族主义的道德观念的支配,所说的一大套实际是很牵强的,译者不敏,未敢苟同)。
少可以把不快之感减到最低限度。这两层,即交接前求爱的准备功夫与交接方式的变换与选择,如果能得充分的注意,我以为大多数女子方面所谓性能薄弱或性趣冷淡的例子已经可以不药而自愈。
上文所说的种种,我们如今渐渐了解,是一个贤明的医师所不能不过问的。我们应知即就受孕一端而论,女子的性的满足也未始不是一部分的条件,因为女子的地位,至少就受孕一点而论,决不是完全被动的。英国前辈中著名的妇科医师邓肯(MatthewsDuncan)认为为保障受孕起见,女子的性快感是万不可少的,后来别的专家如同基希(Kisch)等对这个看法又曾经加以坐实。我们以为性交时快感的有无未必是受孕与否的一个万不可少的条件,因为世间大量的婴儿的孕育,总有一大部分是和这种快感之有无没有关系的;换言之,性交而有快感的女子既少,而婴儿之孕育却如此之多,足征两者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关联。不过基希也发见性感不快的症候(基希认为这是和性交的不得满足是一回事)和女子不生育的现象有很密切的联带关系;他发见38%的不生育女子有这个症候,不过基氏所提到的只是一部分资料,至于一般的情形是否如此,或一般的关联程度是否如此之高,他却略而未论。
上文所谓求爱的准备功夫指的并不是、至少不止是、结婚以前的那一个耳鬓厮磨的阶段,而是每一度性交以前很自然也很必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恋爱艺术里最单纯与基本的一个事实,上文也曾提到过。开始求爱,大抵是男子之事,如果他从察言观色之中,觉得时机是相当成熟,他就不妨建议(他一定得察言观色,时机成熟与否,女子是决不会告诉他的);建议是他,交接前后过程中始终取主动地位的当然也是他;不过如果女子也表示一些主动的倾向,这其间也丝毫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因为假定女子是一百分的被动的话,恋爱的艺术是无从说起的。在纯粹的生理方面,求爱的准备功夫,即一些性爱的戏耍,直接可以引起女子的愉快的情绪,而此种情绪又转而激发生殖器官一带的腺的分泌,总要等到这种分泌相当多,使生殖器官呈一种浸润的状态,才可以开始交接,⑨否则勉强交接也是不愉快的,甚至于有许多困难。有时,因为分泌的缺乏,不能不用滑腻的油脂之类来代替,但如准备的功夫充分的话,这种替代品应该是用不着的。
上文说的这些,在文明社会中虽往往受人忽略,但在所谓不很“进步”的民族里,却了解得很清楚。例如新几内亚的马来人,据说配偶的选择是很自由的(但需不侵犯图腾的界限和血缘的限制),并且男女可以同居好儿个
国风》中所开辟的这个思字的用法,到了后世,也还继续地发展。《方言》十,凡言相怜爱,江滨谓之思,
其实我们根据《国风》立论,思字的这个用法并不限于江滨,我们见到的是《郑风》里最多,但卫、鄘、
周代的王畿等地也有。《山海经》的《大荒东经》说:有司幽之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注:“思
感而气通,无配合而生子”,性的情绪到此境地,也真够缠绵悱恻了。后来的诗人喜欢用“闺思”一类的
题目,描绘“思妇”的情态。由此再进一步,便成不大健全的感伤主义的情绪状态了。《文选》张华《励
志诗》的“吉士思秋”,注:悲也。好比《淮南子》所说,“春女悲,秋士哀”.那思字就等于悲或哀了。
曹植《七哀诗》亦有“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之句。《诗序》上所说“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思字,也
就是这样一个思字。所以就中国文字的源流而言,最接近西洋所称romanticlove的字,不是“恋”,不是
“爱”,而是“思”或后世惯用的“相思”。
⑨说到这里,上文注⑧中所提到的怀字便很有它的地位。《论语》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又说:“少者怀之”。所以译者以为假如男女间的情爱依然可以用思字来代表,则亲子间的情爱可以用怀
字来代表。
月以后才提到婚姻的缔结。有几个地方,又流行着一种风俗,就是男女青年可以同卧,男的可以把女的抱在怀里,同时对于女的上半身可以有抚弄的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交接的行为倒也难得发生,但若发生,随后这一对男女也就议亲而成夫妇。①这一类的风俗,至少对恋爱艺术的一些基本原则是顾到了的。
交接前求爱的准备功夫的过程中又有很自然而也很需要的一点,就是在女子的阴蒂上,多少要运用接触、挤压或揉擦一类的方法来加以刺激,因为阴蒂始终是女子性感觉的主要汇点。②有的精神分析学派的人认为阴蒂之所以为此种汇点,只限于女子性发育的最初几年,一到成年期,正常的情形是这种汇点会从阴蒂转移到阴道,并且事实也往往如此。这种见解究不知从何而来,此派的人每多闭门造车的见解,我以为他们对女子的身心结构,如有几分真知的见,这种见解是很容易消除的。阴蒂是性感觉的正常的汇点,起初如此,后来也未尝不如此,并且往往不但是主要的汇点,而且是惟一的汇点。女子到了成年,在性交生活确立以后,阴道会自成一个性快感的中心,也是很自然的,但其间说不上什么“转移”。狄更生以妇科专家权威的资格说:“就一大部分的女子而论,只有在阴蒂部分感受到压力以后,性交时才能达到亢进的境界,而这是完全正常的。”
说到交接的方式或姿势,有人以为正常而合理的姿势只有一种,就是女子平卧面上,而任何别的姿势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邪僻”的“作孽”的。①那是一个错误。人类历史中某一时代或某一民族所最通行的习惯未必就可以成为天下万世的师法。人类最古的一幅交接的图画是在法国西南部的多尔多涅(Dordogne)地方发见的;它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一个文化期——所谓索留特累期(Solu-trianAge)。在这幅图里,平卧面上的是男子,而女子则取一种蹲踞的姿势。就现状论,不同的民族中,对交接的姿势,就各有其不同的习惯或风尚,而同一民族中,所采用的也大都不止一种姿势。②近时美国医师范·德·弗尔德讲到欧洲人的性生活时说,做丈夫的大都不知道床第生活的单调,如果知道,此种单调的生活是可以用姿势的改换来解除的,而姿势的改换事实上也没有越出正常的变异范围之外;可惜的是,他们大都根本不了解这一点,或虽知其可能,而认为只有“淫秽”的人才肯这样做,他自己是不屑为之的。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说更多一些的话。对许多例子,只需选定一种姿势,问题就可以解决,但对另一些例子,问题要比较严重。
就一部分女子而言,有几种姿势,甚至包括最寻常的几种姿势在内,是根本不容易采用的,或勉强采用了,也可以感到极大的不舒适,而一种比较奇特的姿势反而比较容易,反而比较可以供给快感。
我们说到最广义的生理方面的性关系,我们还得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凡属对于夫妇双方能增加满足与解除欲念的一切行为与方式,全都是好的,对的,而且是十足的正常的;惟一除外的条件是,只要这种行为与方式
①见克芳莱和吉布森在《宗教与伦理的百科全书》中合著的《恋爱》与《初民的恋爱》两段释文。
②精神分析派的这个见地不能说全错,不过把问题看得过于单纯,是不相宜的。爱憎的心理不容易截然划
分。《论语》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之语;《管子·枢言篇》也说:“爱者,憎之始也”。
①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中,只有佛家在这一点上是一贯的,是充类至尽的,它否定恋爱,也根本否定生命。
②基督教《新约·约翰福音》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③关于本节,又可参看:
不引起身心两方面的创伤。(而就身心健全的人而言,这种创伤也自不至于发生,我们可以不必过虑。)寻常的交接而外,更有两种主要的接触,一是女对男的咂阳,二是男对女的舔阴。这种吮咂的冲动是很自然的,即在从未听人道及过的男女,兴会所至,也往往会无端地自动地想到。我发见一般神经不大幢全而道德成见又很深的人不断地发问,这种或那种不大寻常的性接触的方式是不是有害的,或是不是一种罪过。对于这种人,这一类的方式可以引起一番神经上的震撼,他们认为至少“从审美的”立场而言,这种方式可以叫人作三日呕。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就是,所谓最寻常与最受人公认的性交方式又何尝“美观”呢?他们应当了解,在恋爱的神秘领域里,特别是到达床第之私的亲昵境界以后,一切科学与美学的冷静而抽象的观点,除非同时有其他特殊的人文的情绪在旁活动,照例是不再有地位的,有了也是不配称的。一般板执而讲求形式主义的人,一到性的题目上,尽管美意有余,总嫌理解不足,我们对他们,只是很婉转地把莎翁的一句百读不厌的老话提醒给他们听:“恋爱说起话来,自有它的更善的知识,而知识说起话来,总充满着更亲密的爱。”①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妨补充一些事实。汉密尔顿在所调查的100个已婚女子——全都不能不假定为很正常、健康而社会身分很好的女子——中,发见13个有过舔阴或咂阳的经验,或两者兼有,而13个例子都没有发生过不良的影响。因此,汉氏很合理地作结论说:“无论何种性的戏耍的方式,就心理的立场而言,是没有禁忌的。”同时,汉氏也说了一些保留的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此种戏耍在身体上不引起什么创伤,二是在心理上不引起什么罪孽的感觉。这都是很有意义的。汉氏也说到他在别处遇见过一些憨态可掬的例子,他们很天真烂漫地采用过这些所谓“作孽的”性的接触方式,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方式在许多人看来是如何的龌龊,如何的凶险,如何的不得了,“一旦忽然发见这许多人的看法,一番震惊之余,不免深自懊恼追悔,结果很快地促成了一些癫狂的症候”。:即此一端,已足够教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让一般人,在这一类性的问题上,得到一些更开明的见解。狄更生,根据他多年的妇科经验,很贤明地说过,我们应当让每一个女子“可以放心地了解,夫妇之间,床第之私,在高涨的热情弥漫充塞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和精神恋爱的最高理想根本上不相称的;换言之,夫妇之际,一切相互的亲昵行为是没有不对的”。
在这样一本引论性质的书里,我们并没有讨论恋爱的艺术的种种细节的必要。不过在结论里,我们至少应当说明,恋爱的艺术绝对不限于身体与生理的方面。即使我们把生理的方面搁过不论,或虽论而认为它只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即使就成婚已经二三十年而性的生活已退居背景的例子而论,甚至即就根本不能有性交生活的夫妇而论,恋爱的艺术依然不失为一种艺术,一种不容易的艺术。夫夫妇妇之间,应当彼此承认个人的自由;生活理想尽管大致相似,其间脾气的不同、兴趣的互异,也应当彼此优容;彼此应当不断地体贴,应当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弱点与错误,同时也接受对方的错误与弱点,而不以为件;嫉妒的心理是有先天自然的根据的;任何人不能完全避免,偶然的表现是一定有的,并且表现的方式也不一而足,这种表现在一方固然应当力求自制,在对方也应当充分宽恕——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尽管与狭义
:《爱的成年》,有中译本。
的性关系无干,也未始不是恋爱艺术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最大的一部分。并且,若有一分疏虞,不但夫妇的关系受影响,全部的人生艺术也就从此可以发生漏洞,成为种种悲哀愁苦的源泉。
总之,我们对夫妇的关系,总需取一个更宽大的看法;否则,我们对构成此种关系之种种因素,使此种关系的意义更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的种种因素,便无法完全把握得住。一定要这些因素都有一个着落,个人的幸福才有真正的保障,而除了个人的卫生上的功用而外,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也就取得了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婚姻的维持与巩固也就根本建筑在这些因素上。弗洛伊德在1908年时说:“要在性的题目与婚姻的题目上提出改革的方案来,那并不是医师应有的任务。”这种置身事外的看法现在是过去了,而弗氏自己后来也似乎看到这一点,因为,自从1908年以后,他在许多人生的大题目上,可以说一些含义再广没有的大题目上,下过不少思考,发过不少议论。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叫穿他说,医师的任务决不在保留一部分人间的罪孽,为的是可以借题发挥,甚至可以于中取利;这种看法尽管和医术的原始的看法完全相反,但时代既大有不同,我们的观念也自不宜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在医学的每一个部门里,医师和一般明白摄生之道的人的任务就在对人生的种种条件与情境,求得进一步的调整与适应,务使“罪孽”的发生越少越好,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部门里,我们的任务更应如此,因为它和人生的关系要比任何其他部门更见得密切,而其为祸为福,所关更是非同小可。因此,医师对于任何医学的部门虽应有充分的认识与运用充分的聪明智慧,而对于我们目前所注意的部门,尤其应当如此。
基(EllenKey):《恋爱与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