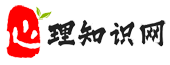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黄金时代》的叙事空间:《黄金时代》有“被朗诵出的女文青的一生”之称,朗诵成为解读该片的关键词。首先必须承认的是,作为一个英年早逝的女作家,萧红并非一个很好塑造的人物,关于她的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抑或是在她的个人生活上。为此,许鞍华寻找到一种多维度、多方面、多声道的叙事方式,从个人回忆、亲友的记忆与观察以及国民女作家传奇三个声音方面来解析萧红。
《黄金时代》的风格是纪录片式的,影片的叙事空间主要建立在真中有假、假中求真的访谈式场景中,使用了大量的亲友采访,模仿纪录片式的镜头。影片通过萧红及他人往来信件的复述,以及萧红本人的自述这样的桥段和摄影手法来构建和串联事件,达到了一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就人物而言,影片中的“亲历者”和“回忆者”事实上都是演员,本身就是剧情的参与部分,而故事的呈现形式又是剧情片与纪录片相混合的,这样就制造了一种虚构中存在真实再现,真实再现中又带有仿拟成分的审美效果。这也正是当下许多观众感到困惑的,当情节正在进行时,许鞍华就会将镜头一转,让前面情节的参与者端坐着对萧红的生平以及当时的情况娓娓道来,带给观众一种心理阻拒,不断地进行着“进入剧情―离开剧情―再进入剧情”的过程。甚至二者合一,比如聂绀弩在进行有关上海复杂的政治情况的回忆时,演员身后的剧情依然在继续。又如在表现萧红与萧军观看白朗等人排演戏剧,大家乐不可支,随后是冬天的雪夜里,几个文艺青年手挽手走在雪地上,互相用俄语大喊着新年快乐时,镜头随即切换到了萧红对端木蕻良进行回忆的场景。萧红颇有点黯然地对端木说,他们后来还请了一个俄国老师来教大家俄文,后来萧军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是一个姓程的中学生。用短短的一两句话就迅速将观众的情绪从前面营造的轻松氛围中拉出来,引发观众的思考。这里采用的是萧红本人的叙述方式,与其说是在对端木诉说,还不如说是一次颇有些不合时宜的呓语式独白。而他人如许广平、白朗等人对萧红的回忆画面也比比皆是。在影片中,无论是正片的叙述抑或是访谈部分,大部分的场景都发生在室内,许鞍华往往采用晃动的镜头,配上昏黄的灯光,加之身上穿着臃肿冬装的萧红与萧军,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和时代感,即使是在偶尔的外景中,许鞍华也多采用近景和中景镜头来保持这种压抑感。这种压抑感一部分是服务于表现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时的苦中作乐,另一部分也是让观众感受萧红的心境。
许鞍华正是想凭借这样的结构来突出一种纪录片式的自然、客观和公允,以及导演对大局的控制。因为围绕萧红的话题,无论是时代、人物抑或文学,都是极难把握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如同拍摄霍金的传记片一般,人们关注的仅仅是传主的婚姻和性。这对于萧红来说无疑是悲哀的。与同时代的其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不同的是,萧红的一生是主动选择噩运的一生,无论是逃婚、结婚、离家出走、去香港等,她都是主动将自己放逐在一个凶多吉少的未知环境中。萧红不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人,而宁可在无常的命运中寻求到一点自己做主的可能。换言之,萧红是拒绝成为男权社会中的消费品的。然而在男权社会依然存在并且是社会主流的今天,萧红所被消费的仍然是她的私生活、她的身体,而远远不是她在文学上的才华。一旦许鞍华采用纯粹的故事片的形式对萧红一生进行按部就班的叙述,大众的注意力必然就很容易脱离导演原本的意图,从而产生种种不必要的误会,比如将注意力都集中在萧军三番五次的家庭暴力和出轨这些负面内容上。这正体现出了许鞍华一向以来对女性的悲悯情怀。[2]但是对于观众来说,则只会认为《黄金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满足许鞍华和李樯的个人野心,甚至在情节的安排上显得有些颠三倒四。诚然,《黄金时代》在讲故事方面并不纯粹,但是其艺术独创性是难能可贵的,真正了解萧红生平的人,依然能为这部电影结结实实地感动。
《黄金时代》的叙事空间
2023-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