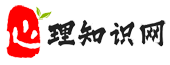乡村里的恋土情结和传统道德:新中国建立之时,路遥出生于陕北农村,在十七岁之前甚至没有走出过县城,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青少年时期。陕北的黄土地无疑是路遥的情绪磁场和创作源泉。对土地的依赖,对陕北农民深沉热烈的眷恋,以及对民间传统道德的认同,形成了路遥最稳定的心理特征,从而产生无意识的创作冲动。陕北黄土高原在路遥的意识世界里不单纯是种庄稼的土地,它远远超出了农村与农业的概念范畴,可以概括为三种时空、内涵层次不同的意义:
一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农村与农业,或准确一点说,指农村社区生活和弥漫于其间的传统农业文化。陕北黄土高原一带数千年来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当地的居民们过着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种地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土地的质量和粮食的产量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状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利希?波尔曾经说过:“你们中国人有一种对土地的健康意识――人属于脚下这块地。”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陕北人一生都离不开黄土地,世世代代忠实地守着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路遥的父母是千万陕北老农中普通的一对,卑微老实,整日在烈日下劳作,在干旱的黄土地上求得稀缺的粮食。因此,黄土地上农家出生的作家路遥,一生倾诉了对黄土地深深的依恋。在写作时,路遥经常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直到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路遥在稿纸上的“精耕细作”和陕北农民在黄土地上的刨挖耕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中途,身患重病,回到故里,瞬时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得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他始终相信一句名言:“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在《平凡的世界》里对陕北黄土高原充满感情的描摹随处可见,“铺张”到近乎炫耀,从不吝啬自己的激情和语言,从不掩饰内心对这片黄土的热爱。
二是与土地、与底层生活实践相关联的父母、亲朋、家族,甚至于基层干部的综合,可称之为“土地―母亲―人民―劳动实践”形象系列。在路遥的笔下,老实巴交、勤勉善良的陕北农民是经常被刻画的形象。路遥早年生活十分贫困,在最困难日子里,凭借周围乡亲的关爱和资助得以读完中学。因此,对于黄土地上的人民,路遥始终有一种深切的感情,他一方面把笔下的人物当成自己的父辈和兄弟姐妹一样,对其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同时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不幸。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饱含感情地描写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他们大多生活困窘,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明晓做人的基本准则,相互尊重,在对方陷入困境时能够相互帮扶,善意待人。即使是小农意识强烈的田福堂,善于钻营但又活的窝窝囊囊的孙玉亭、四处浪荡一事无成的王满银,抑或是疯疯癫癫的田二,作者都没有对他们进行极端的批判和否定,对于他们,读来没有丝毫憎恶,概叹之余反而可以找到一些人性的闪光点,作者对他们只有理解,没有丑化和嘲弄。
三是陕北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构成了路遥的生活体验情境,使路遥产生了对道德、情感主题的认同,同时成为路遥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为后期的创作积累了素材资料,交代了路遥的心路历程变迁,指明了其精神家园的去向。陕北地理位置偏僻,地形独特,与同属三秦大地的关中迥异,同时也独立于与之毗邻的内蒙,鲜与外界接触流通,至今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原始的文化形态,儒家意识尤其明显地浸润着这方土地,长期生活于此的路遥不能不受此濡染:首先是孝悌。孙玉厚一家虽然生活极其窘迫,但是心性善良、诚信待人,在街坊邻里间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家庭成员内部更是在相互关切、帮扶中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数以万计的陕北农民家庭的缩影;其次是仁义。重义轻利在孙少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他办砖厂开始发家致富时,同村的人向他救助,他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想尽办法扩大砖厂规模,从而能够提供更多的职位解决村民的燃眉之急;还有孙少平,在工地打工时,遇到弱女子小翠被包工头欺负,当即挺身而出。还有“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田福军身上体现着整部小说中最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与孙少平精神相通,融汇于巨大的“暖流”,他是人文传统培养出来的,恪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士阶层人格精神的典范。小说以充分的地域文化特征来表现人文,以黄土地精神来表现民族精神,描写孙少安做出出资办教育的壮举,是接受了这块土地上一种“历史意识”的支配,是精通孔孟学说的金先生的儒家人生,启示了他,使他领悟了一种使命。“东拉河一带像他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如果有识字知书者,都是受惠于这位老先生,连赫赫有名的田福军,也是在金先生膝下完成的启蒙教育……”[2]在《平凡的世界》中,大多数人都恪守着传统的道德伦理以及良好的生活品行,这在现在浮躁的都市中显得弥足可贵。
乡村里的恋土情结和传统道德
2023-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