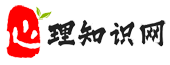③此举的合理,是显而易见的,初无待乎特别的申说。纳客(Naecke)说,“学校男女儿童在这方面的训
海,最宜乎请老成的医师来担任。”克劳士顿(Clouston)在《心理的卫生》(TheHygieneofMind)山,
第249页上,也说,“我竭力主张请家庭的医师、来担任这种责任,有了父母和学校教师左右加以辅翼,他确乎是一个最好的劝导和告戒的人。”冒尔也有同样的意见。
固然已经一天比一天的呆板,已经从有意义的活动变做无意义的僵尸。但实际上它们还是有价值的,我们要把它们的活力挽回转来,也并不是不可能。同时我们也不要把这种仪式的精神与意义和超自然主义的与凭籍启示的宗教混为一谈,以为惟有此种宗教才能有这种精义。要知洗礼与坚信礼一类的仪节虽属于神道的宗教,而大觉大悟的心灵的转变却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在神道的宗教以外,同样的可以找到。所以一切在道德或伦理方面做导师的人,在这时期里都应该特别注意与努力。他们应该了解春机发动期是种种高大的理想与志愿自然而然会在男女青年的心灵上发生的时期,而他们的任务就在贡献一些精神上的感奋与扶持,使此种理想与志愿不至于苗而不秀、秀而不实①。
我在上文讲的种种全都是适用于春机发动期已经开始以后。至若在春机发动以前,比较精神方面的恋爱的情绪虽往往已经逐渐发展,甚至于生理方面的恋爱的情绪有时也模糊隐约的可以经验到,但确切不移并且限于一二器官的性的感觉总究是希有的。对于发育健全的男童或女童,恋爱大都是一种比较笼统散漫而还没有专门化的感觉或情绪;瞿瑶(Guyau)说得好,它是“一种状态,在此种状态中肉体所占的地位是极小的。”诗人勃雷克(Blake)所描写的日出的情景,也可以引来做一个很妙的譬喻;在性的太阳在东方初出的时候,一个男青年或女青年所见从天际冉冉上升的并不是一个浑圆的黄色的球,也并不是其它什么物质的现象,而是一群歌唱着的天使。但在体内的性的冲动与欲望初次很明白的感觉到以后,一种新的扰乱心神的影响就应运而生了;此种冲动之来也许在春机发动的时候,也许在后来的成年期以内,但其为足以扰乱心神则一。要对付这种新的影响,只是一点理智上的启发排解,也许就无能为力,就是母氏的爱护备至的一点叮咛告诫也未必有多大效果。这两种力量,我们在上文都已经充分讨论过,到此既已都不适用,我们便不能不考求第三种的力量了。这第三种可以帮忙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刚才正在讨论的精神生活的激发。我们总得明了,春机发动中所指的春机,不但指一种新的生理上的力,也指着一种新的精神上的力。这精神上的力便是我们目前的救星了。惟有这新的精神上的力才能制裁那新的生理上的力。在春机发动期内,理想的世界便自然会在男女青年的面前像春云般的开展出来,审美的神妙的能力、羞恶的本性、克己自制力的天然流露、爱人与不自私的观念、责任的意义、对于诗和艺术的初步的爱好——这些在这时候便都会在一个发育健全、天真未失的男女青年的心灵上,自然呈现出来。我用“天真未失”四个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过是指在这个时期以前,父母或其他长辈没有把这许多东西强制的堆砌在青年的心灵上。要是以前有过勉强堆砌的痕迹,那未,到他真正可以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许反而不会作自然的与正当的反应。不幸世俗的父母师保大都不明此理,往往在这些地方采用强制的手段,尤其是在宗教观念方面,也无怪春机发动期内真正发育健全的人的不多了。但在比较自然的社会状态之下,春机发动期也就是最宜于精神生活启蒙与诱掖的时候。宗教或伦理的导师在这时候便不妨把引导青年的责任负担起来,他的最大的目的是在扶植他们的精神上的发育,他也尽可以谈论到生理与性的一方面,但是谈论的方法应随机应变,而不宜草率,谈
①我以前在《宗教与儿童》(ReligionandtheChild)一文中,曾于此点加以发挥,见《十九世纪与以后》,(NineteethCenturyandAfter),1907年卷。
论的用意也并不在增加他们的知识,而在帮助他们使自己可以运用上文所提的新兴的精神的力量,来制裁新兴的生理的与性的力量,以免走人歧途,或沉而于逸乐而不知自返。所以我们在上文说,新兴的精神的力是这时期里一大救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宗教或伦理导师,不用说,自然也并不限于任何一种特殊的宗教或伦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