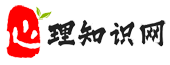媚俗的释义与心理机制:从大众文化的接受来讲,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雅俗共赏”,然而这里提到的“俗”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世俗和通俗,是人世间平凡而美好的一种情感和生活,而我们今天要谈的“俗”则指的是庸俗、低俗和鄙俗。媚是指谄媚,卑贱的迎合与讨好,而讨好的是那些不符合大众审美,不能登大雅之堂,不具有正能量的蝇营琐事。古今中外人们对文艺作品的评判标准向来都是“崇雅贬俗”。明代高启《妫?V子歌为王宗常赋》中就提到:“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显示出了不向“恶俗”低头的决心。齐白石先生也曾经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讲的也是对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中欧四杰”之一的奥地利着名作家赫拉曼?布洛赫对媚俗的阐发更是一针见血,他说:“每一个文化衰落的时代就是媚俗大行其道的时代。”[4]他把“媚俗”行为定义成一种“极端的恶”,已经完全走上了与艺术标准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他认为媚俗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伦理范畴与美学范畴理解的错位,媚俗的目标是“美”,而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善”,这种思想与我国先秦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的理论遥相呼应。孔子认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韶》才是“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所说的“美”自然是审美标准,而“善”则指的是道德标准,只有既符合审美标准又符合道德标准的艺术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以至于“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在布洛赫《恶的代表》一文中,他更是对媚俗的本质做了全面的揭露:“正是这种利用有限和理性的手段满足欲望的方式,正是这种有限被吹嘘抬升为无限以及对‘美’的径直追求,使得媚俗被蒙上了不诚实的面纱,而躲藏其后的就是为人们所诟病的伦理道德之‘恶’。”更是毫不留情地痛斥媚俗的制造者们,称他们为“道德败坏者”和“作恶的罪人”[4]。由此可见,艺术作品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审美问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内容。
媚俗的艺术产品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也有着它深刻的心理根源。早期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汉斯?萨克斯在1932年发表的文章《媚俗》中探索了媚俗作为个体和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媚俗的心理动因是契合了受众内在的“移情动力”,通过移情的作用,将“力比多”转移,为其找到情绪体验的替代对象,得到一种代偿性的满足。而“媚俗”的作品恰巧符合了这种需求,它简单易懂,不制造复杂的心理情境,不给受众以思考的压力,使受众在轻松简单的语境中迅速做出心理抉择,其心理机制与“白日梦”有着极为相似的形态与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的特奥多?阿多诺擅长分析音乐中的媚俗现象,他从媚俗的音乐中听到了“一种创作上的惰性”,是创作上的一种中庸之道,媚俗的艺术作品有着文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同质性”,缺乏自己的鲜明个性,而伟大的艺术品则应是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都会在风格上实现一种自我否定。
德国哲学家吉斯从人本美学出发,着眼于媚俗的主观体验,并以“过度伤感”来概括对媚俗的体验方式和意识状态,认为媚俗之人在对媚俗作品进行体验的过程中会臆想出一些无名的感动,进而为了感动而感动,倾心于自我感动的情绪体验之中。这是一种充满媚俗状态的虚伪态度,抛弃了传统审美体验中的距离感而构筑一种虚假的一体化的审美体验,最终导致对艺术作品的媚俗解读。
中西方对媚俗的理解原本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自从西方20世纪60年代起波普艺术以及杜尚当代行为艺术流行之后,高雅与低俗、艺术与媚俗之间的分野似乎已变得模糊不清,表现为艺术对资本,高雅文化对商业和消费文化的释然拥抱。近年来,西方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影视领域开始盛行一股“媚俗”风潮。“‘媚俗’概念被一群风格各异的思考者推动着,从‘垃圾艺术’‘极端之恶’的唾弃声中爬起,搭乘商品与消费文化的顺风车,朝着享乐主义的世俗化奔驰,有如一场脱冕、降格、戏拟式的狂欢,沿着身体与物质的方向径直下坠。”[4]
毋庸讳言,文化产品有着其特殊的“双重属性”,它既是供人们消费的商品,同时还是诉诸人们精神领域的文化产品,它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当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它是提升国民素质,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领地,所以,我们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媚俗的释义与心理机制
2023-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