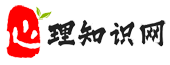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性的教育》译序:译了《性的教育》以后,进而续译霭氏的《性道德论》,似乎是很合情理的,性教育的效果所及,以个人方面为多,性道德的,则以社会方面为大。性教育是比较现实的,性道德是比较理想的。由个人推而至社会,由现在推而至未来,所以说很合情理。
霭氏的《性道德论》,实在有五根柱石:
一、婚姻自由
二、女子经济独立
三、不生有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干
四、女子性责任自负自决
五、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女
这五根柱石的实质与形式,具详本文,无须重复的介绍。不过它们的价值,不妨在此估量一下。
一、婚姻自由的理论,我想谁都不会持异议。不过有两点应该注意。西洋的婚姻制度,历来受两种势力的束缚,一是宗教,二是法律,这法律的一部分又是从宗教中来,所以束缚的力量是分外的大。唯其如此,霭氏在这方面的议论,便不能不特别的多;好比因为西洋人对于性的现象根本认为龌龊的缘故,他就不能不先做一大番清道夫的工作一样。这是一点。霭氏这里所称的自由,似乎目的端在取消宗教、法律与其它外来的束缚,是很消极的;至于怎样积极的运用自由,使婚姻生活的效果对于个人、对于社会、以至于对种族,可以更加美满,蔼氏却没有讨论到。而所谓“积极的运用”里面,往往自身就包含相当客观条件的节制,这一层霭氏也没有理会。自由是应该受客观条件的范围的,否则便等于自放,等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没有不遭灭顶的惨祸的。霭氏在下文说(7—8页):“往往有很有经验的男子,到选择女子做妻子的时候,便会手不应心、身不由主起来;他最后挑选到的结果未始不是一个很有才貌的女子,但是和他的最初的期望相较,也许会南辕北辙似的丝毫合不拢来。这真是一件奇事,并且是万古常新的奇事”。霭氏写这几句的时候,也许精神分析派的心理学说还不大发达,从这一派学说看来,这种手不应心的婚姻选择实在并不是一件奇事,并且只要当事人在事前稍稍受一些别人的经验的指导,即稍稍受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完全诉诸自由行动,它就不会发生。这是第二点。就中国与今日的形势而论,我以为第一我们不必像霭氏那般的认真。中国以前的婚姻,也是不自由的,但是束缚的由来,不是宗教,也不是法律,而是家族主义的种种要求,无论这种种要求的力量在以前多大,到现在已经逐渐消散,而消散的速率要比西洋宗教与法律的还要来得快。结果,尤其在大一些的都会里,不自由已一变而为太过自由,而成为一种颓废的自放。好比自鸣钟的摆一般,以前走的是一个极端,现在又是一个极端。要挽救以前的极端,我们固不能不讲些自由,要免除目前的极端,更不能不讲求些客观条件的节制。霭氏所自出的民族,是一个推尊个人与渴爱自由的民族,所以他的议论也很自然的侧重那一方面。但我们的文化背景与民族性格未必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完全相同,斟酌采择,固属相宜,全部效颦,可以不必。
二、女子经济应否独立的一个问题,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的;但究宜独立到何种程度,和男子比较起来,是不是宜乎完全相等,还始终是一个悬案。霭理士在这一方面的议论,好比他在别的方面一样,是很周到的。
在原则方面,他不但完全承认,并且把它认为讲求性道德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过在实际上他也认为有很严重的困难。霭氏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原是西方女权运动最热烈的时候,但是热烈的空气并没有蒙蔽他的视线,别人也许忙着替极端的男女平等论鼓吹,心切于求、目眩于视的把男女生理作用的区别完全搁过一边,认为无关宏旨,但是霭氏没有。他说:
但上文种种还不过是一面的理论。女子的加入工业生活,并且加入后所处的环境叉复和男子大同小异,这其间也就无疑的引起了另一派的严重的问题。文化的一般的倾向是要教女子经济独立,也要教她负道德的责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是男子所有的职业以及种种业余职务,女子都得参加,都得引为己任,而后不但女子自身可得充分发展之益,而社会全盘亦可收十足生产之功,我们却还不能绝对的看个清楚。但有两件事实很清楚。
第一、社会现有的种种职业与业余职务既一向为男子所专擅,则可知它们的内容和设备的发展是在在以男子的品格与兴趣做参考,而与女子太不相谋。
第二、种族绵延的任务与此种任务所唤起的性的作用,在女子方面所要求的时间与精力,不知要比男子的大上多少。有此两点的限制,至少我们可以了解,女子之于工业生活,决不能像男子的可以全神贯注,而无遗憾。
不能无遗憾的话是对的,二十几年前,霭氏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种遗憾还不很明显,但男女职业平等的试验又添上二十多年的经验以后,这种遗憾已一变而为切肤的痛苦。英人蒲士(MeyrickBooih)在他的《妇女与社会)(WomanandSociety,即刘译《妇女解放新论》)一书里,在这方面讨论得最精到。霭氏那时候,因为情形还不严重,但在我们看来,以为它的重要并不在其它段落之下。
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女子职业自由与经济独立的问题,实在已经可以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办法。在原则下它是毫无疑问,上文早就说过。就实际而论,我们折衷近年来一部分通人的见地,以为有一种看法与两三种办法,值得提出来商量。一、就健全的女子而论,我们总得承认生育是她们一生最主要的任务,不论为她们自身的健康计,或为种族全般的发展计,这任务都是绝对少不得的。至少就她们说,——不就她们说,又就谁说——职业的活动与经济的生产只得看做一件附属的任务,一件行有余力方才从事的任务。这是看法。由这看法,便产生下列的一些办法。无论一个女子将来从事职业与否,她应该有一种职业的准备,应该培植一种经济生产的能力。宁使她备而不用,却不能不备。在她受教育的时期里,除了普通的教育以外一切有职业训练的机会,也应当为她开着,就是那些平日专为男子而设的,也不应稍存歧视的态度,目的是在让她们各就性之所近,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同时我们当然不希望一班极端的女权运动者出来吹打鼓噪,因为这种吹打鼓噪的功夫也未始不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障碍。有了职业与经济独立的准备,用也行不用也行,要用的活,我们以为不妨采取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一是直接适用上文所提宾主的看法的结果。一个精力特强的女子,尽可于生育与教养子女之外,同时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的事业,但总以不妨碍子女的养育为限;二是精力寻常或觉得同时不能兼顾两种工作的女子便不妨采取罗素夫人
所提的分期办法,就是,在婚姻以后,最初十年间或十五年作为养育子女的时期,过此便是从事职业的时期。这两个办法,我认为都很妥当。这两个办法又可以并做一个说,就是上文所说宾主的地位到了后来,不妨逐渐地对掉,起初养育子女的工作是绝对的主,後来子女渐长,不妨变做相对的主,到了子女都能进学校以后,职业的活动即作“夺主”的“喧宾”,亦无不可。
三、霭民主张凡是不生育的性行为、性结合,与社会无干,社会不当顾问。这个主张可以说是富有革命性的。西洋社会对于这种主张,到现在当然还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在赞成的少数人中间,在美国我们至少可以举一个做过三十年青年法庭的推事林赛(B.B.Lindsey)。在英国,则至少有哲学家罗素。他根据了三十年间应付青年性问题的经验,起初做了一本《现代青年的反抗》(TheRevoltofMndernYouth,1925),所谓反抗,十分之九是对于旧的性道德观念的反抗,对不合情理的宗教、法律、与社会制裁的反抗;全书的理论与所举的实例,几乎全部可以做霭氏的“婚姻自由论”的注脚。林氏后来又发表一本《伴侣婚姻》(ChmpenionateMar-riage,1927)。要是《反抗》一书所叙的是问题,这本书所要贡献的便是问题的解决方法了。这方法是很简单的,就是:男女以伴侣方式的结合始,一到有了子女:才成为正常的婚姻,在没有子女以前。双方离合,却可不受任何限制。所谓伴侣的方式,就是一面尽可以有性交的关系,而子女来到的迟早则不妨参考绎济和其它的环境情况,运用生育节制的方法,而加以自觉的决定。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完全脱胎于霭氏的学说的。罗素的见地则详他的《婚姻与道德》一书中(MarriageandMorals,1929,中译本改称为《婚姻革命》),大体上和林氏的没有分别。
至于反面的论调,我们至少可以举马戈尔德(C,w.Margold做代表。他做了一本专书,叫做《性自由与社会制裁》(SexFreedomandAsialControl,1926)。马氏以为人类一切行为都有它们的社会的关系,性行为尤其是不能做例外,初不问此种行为的目的在不在子女的产生。他以为霭氏在性心理学方面,虽有极大的贡献,但因为他太侧重生物自然与个人自由,对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制裁一类的问题,平日太少注意,所以才有这种偏激的主张。这是马氏的驳论的大意;他还举了不少从野蛮、半开化,以及开化的民族的种种经验,以示社会制裁的无微不入、无远弗届。
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做一个详细一点的讨论,并且很想贡献一种平议,但现在还非其时。不过这平议的大旨是不妨先在这里提出的。霭氏因为看重个人自由,所以把性道德建筑在个人责任心的基石之上,因为看重生物的事实,所以主张自然冲动的舒展,主张让它们自动的调节,而自归于平衡。自然的冲动既然有这种不抑则不扬、不压迫则不溃决的趋势,那末,只要再加上一些个人意志上的努力,即加上一些责任心的培植,一种良好的性道德的局面是不难产生与维持的。这种见地,我以为大体上虽可以接受,却有两个限制。一是霭氏所假定的对象是去自然未远的身心十分健全的人,这种人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似乎并不很多。他们自然冲动的表现,不是不够,便是过火,而能因调剂有方、发皆中节的,实在并不多见。中国古代的圣哲不能不说“不得中行而与,必也狂捐”的话,原因也就在此。第二个限制是责任心的产生似乎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究竟应该用甚么方法来培植它,霭氏也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是马氏和其他特别看重社会制裁的人的错误在过于侧重外力的扶持,霭氏的错误就在太责成个人,而同时对于个人自己制裁的 能力,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保障。
性道德应以社会为归宿的对象,是不错的,应以个人的自我制裁做出发点,也是不错的。制裁不能不靠责任心的培植,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但制裁与责任心的养成,一面固然靠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一面也不能完全不仗外力的扶持。但这层霭氏却没有完全顾到。但所谓外力,我以为并不是一时代的社会的舆论,更不是东西邻舍的冷讥热笑,而是历史相传文化的经验。这又是马氏的观察所未能到家的地方,说到这里,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训就有它的用处了。以前儒家讲求应付情欲的方法,最重一个分寸的节字(后世守节的节字己完全失却本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便是这节字的注脚,我们和西洋的宗教人士不同,并不禁止一个人情欲的发动,和西洋的自然主义者也不同,并不要求他发动到一个推车撞壁的地步,但盼望他要发而中节、适可而止,止乎礼义的义字便等于宜字,等于适可而止。这适可的程度当然要看形势而定。夫妇之间的性生活的适可程度是一种,男女朋友之间的当然又是一种。张三看见朋友李四的妻子,年轻、美貌、人品端庄”便不由得不怦然心动,不免兴“恨不相逢未嫁时”之感。这就叫做“发乎情”。情之既发,要叫它立刻抑止下去,事实上当然不能,理论上也大可不必”要让它完全跟着冲动走,丝毫不加枫阻,势必至于引起许多别的问题,非特别喜欢多事的人也决不肯轻于尝试。所以张三要是真懂得情理的话,就应当自己节制自己,他尽可队增加他敬爱李四妻了的程度,提高他和他何的友谊关系,而不再作“非分”之想。那“非分”的“分”就是“分寸”的“分”,这就叫做“止乎礼义”。发乎情是自然的倾向”止乎义也未始不是”不过是已经加上一番文化经验的火候罢了。“发乎情,止乎礼义”七个字,便。是一种文化,的经验,谁都可队取来受恩,来培植他的自我制裁的能力,来训练他对人对己的责任心肠。
这样一说,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究竟是社会的还是私人的,也就不成为性道德问题的症结,问题的症结在大家能不能实践“发情止义”的原则。西洋社会思想的系碗中间,总有一套拆不穿的”群己权界”的议论,任何道德问题。说来说去,最后总会掉进这权界论的旧辙,再也爬不出来。这在我们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知道此种行为不但不于社会全般的事,更不于第二个旁人,的事,而完全是我个人的操守问题,而此种操守的准绳,既不是社会的毁誉,鬼种的喜怒、宗教的信条、法律的禁例,而是前人经验所诏示的一些中和的常这;中和的常道之一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霭氏曾说(页一五):“我们不会对不起道德,我们只会对不起自己”,发乎情而不能止平礼义,所对不起的不是礼义,不是道德,不是社会,而是自己。
四、关于第四根柱石——女子性责任的自负自决——不比以前的三根,我想谁都认为是毫无问题的。性责自负,当然和经济独立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霭氏的理想,大约假定能够实行新性道德的社会,也就是所有的健全妇女经济上能够自给的社会。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略有修正,到此我们更不妨进一步的假定,以为所谓经济独立不一定要完全实在的。在教养子女之余,或教养子女以后,经营一种职业的女子,当然有她的实际的独立,不过在没有余力经营职业的女子,或平日有此余力而适逢分娩的时期以致不能工作的女子,我们始终得承认他们有与经济独立有同等价值的身分。有到这种“等值”(Equiva1ent)的身分,不论她实际赚钱与否,一个女子的责任、权利、与社会地位,便应该和实际从事一种职业的人没有分别。至于性
责自决,也是一样的不成问题。若就生育子女的一部分的责任而论,她不但应该自决,并且应有先决之权。在生育节制方法已经比较流通的今日,这不但是理论上应该、也是事实上容易办到的事。
要女子能够自负自决她的性的责任,经济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教育的条件。也许教育的条件比经济的还要紧,因为经济的条件,往往可以假借,有如上文云云,而教育的条件却绝对不能假借。所谓教育的条件,又可以分为两部分说。第一是一般的做人的教育。这当然是应该和男子的没有分别。这部分的教育也包括专业的训练,目的在使她前途能经济独立,或有独立的“等值”。第二是性的教育,目的在除掉启发性卫生的知识以外,要使她了解女子在这方面的责任,要比男子的不知大上多少倍,并且假若不审慎将事,她在这方面的危险,也比男子要不知大上多少倍。有了第一部分的教育,一个女子就可以取得性责自负的资格;有了第二部分的教育,她更可以练出性责自决的能力。资格与能力具备以后,再加上经济自给的事实或准备,女子在新性道德的局面里,才算有了她应得的女主人的地位。霭氏在全篇议论里,对于这一层似乎没有加以相当的考虑。他对于“性的教育”,固然已另有专篇,但是对于上文所说的第一部分的教育,他既没有讨论,对于这两部分的教育和女子性责自负自决的密切关系,又没有特地指出。这实在是全篇中的一个遗憾。
五、上文说过性道德的对象是社会,但这话还不完全。性道德的最后的对象是未来的社会,若就一人一家而论,便是子女。对于这一点,除了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以外,我想也是谁都不能不首肯的。霭氏说:
就己往、目前、与未来的形势而论,我们便可以得像法国女作家亚当夫人(MadameJulietteAdam)所说的一个综合的观察,就是,己住是男子的权利牺牲了女子,目前是女子权利牺牲了小孩,未来呢,我们总得指望小孩的权利重新把家庭奠定起来(页八五)。又说:
社会要管的是,不是进子宫的是什么、乃是出子官的是什么。多一个小孩,就等于多一个新的公民。既然是一个公民,是社会一分子,社会便有权柄可以要求:第一他得像个样子,可以配在它中间占一个地位;第二他得有一个负责的父亲和
一个负责的母亲,好好的把他介绍进来。所以爱伦凯说,整个儿的性道德,是以小孩子做中心的。
爱伦凯不但这样说,并且还为了这说法写了一本《儿童的世纪》(TheCenturyofChild)的专书咧。
自从优生学说发达以后,子女不但成为性道德的中心,并且有成为一般的道德的对象的趋势。在民族主义发达的国家,这趋势尤其是明显。优生学家有所谓种族伦理的说法,以为伦理一门学问,它的适用的范围,不应以一时代的人物为限,而应推而至于未来的人物。有一位优生学的说容,又鼓吹“忠恕的金律应下逮子孙”的道理。六七年前,我曾经不揣博陋的写了一本《中国的家庭问题》,站的也完全是这个立场。
以子女为最后对象的性道德或一般道德,终究是不错的。我们为什么要生命?不是为的是要取得更大的生命的么?这更大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当然各有各的见解。一班个人主义或享乐主义者以尽量满足一己的欲望为尽了扩大生命的能事;一班狭义的宗教信徒,以避免痛苦于今生,祈取福祉于来世,做一个努力的对象;但是另有一班人以为更大的生命实在就是下一代的子 孙,而使此种生命成为事实的责任,一大部分却在这一代的身上。
***
说到这里,西洋近代的性道德就和中国固有的性道德,慢慢的走上了同一的大路。霭氏在这篇文字里,曾历叙西洋性道德的两种趋势,在中国的历史里,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趋势,读者要知道它梗概,不妨参考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一类的作品,我们不预备在此多说。但这趋势里的最昭昭在人耳日的一点事实,是不能不一提的。就是,子孙的重要。“宜子孙”三个字始终是我们民族道德的最大理想。女子在婚姻上的地位,大众对于结婚、离婚、再蘸、守寡等等行为的看法,虽因时代而很有不同,女子所蒙的幸福或痛苦也因此而大有出入,但最后的评判的标准,总是子女的有无与子女的能不能维持一姓的门楣与一宗的血食。贞操一事,始终似乎是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自身不是目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终究是一两个理学家的私见,而不是民族经验的公言,民族经验的公言是:失节事小,子孙事大。俞抛(曲园)的《右台仙笔馆记》里,记着这样一段故事:
松江邹生,娶妻乔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岁而邹死,乔守志抚孤;家尚小康,颇足自存。而是时粤贼已据苏杭,松江亦陷于贼。乔虑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顾此呱呱者,又非每不活,意未能决。其夜忽梦夫谓之曰:“吾家三世单传,今止此一块肉,吾已请于先亡诸尊长矣;汝宁失节,毋弃孤儿。”乔寤而思之:夫言虽有理,然妇人以节为重,终不可失;意仍未决。其夜又梦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媪,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为汝一身计,则以守节为重,为我一家计,则以存孤为重;愿汝为吾一家计,勿徒为一身计。”妇寤,乃设祭拜其舅姑与夫曰:“吾闻命矣”。后母子皆为贼所得,从贼至苏州。
乔有绝色,为贼所嬖,而乔抱阿九,无一日离。语贼曰:
“若爱妾者,顾兼爱儿,此儿死妾亦死矣”。贼恋其色,竞不夺阿九。久之,以乔为“贞人”,以阿九为“公子”,——“贞人”者,贼妇中之有名号者也。
方是时贼踞苏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尽,雉豚之类,亦皆断种,贼中日用所需,无不以重价买之江北。于是江北诸贫民,率以小舟载杂货渡江,私售于贼。有张秃子者,夫妇二人操是业最久,贼尤信之,予以小旗,凡贼境内,无不可至。乔闻之,乃使人传“贞人”命,召张妻入内与语,使买江北诸物。往来既稔,乃密以情告之,谋与俱亡。乘贼魁赴湖州,伪言己生日,醉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张秃子舟以遁。
舟有贼旗,无谁何者,安稳达江北。而张夫妇意乔居贼中久,必有所赢,侦之无有,颇失望;乃载之杨州,鬻乔于娼家,乔不知也。
娼家率多人篡之去,乔仍抱阿九不释,语娼家曰:“汝家买我者,以我为钱树子耳,此儿死,我亦死,汝家人财两失矣。若听我抚养此儿,则我故失行之妇,岂当复论名节”。娼家然之。乔居娼家数年,阿九亦长成,乔自以缠头资为束修、傅阿九从塾师读。
俄而贼平,乔自蓄钱偿娼家赎身,挈阿九归松江,从其兄弟以居。阿九长,为娶妇;乃复设祭拜舅姑与夫曰:“■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贞人,继为娼,尚何百目复生人世乎?”继而死。
俞曲园曰:“此妇人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节,不失为完人。程子
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我记得以前看见这一段笔记的时候,在“天头”上注着说,推此论而用之于民族,虽千万世不绝可也。”我现在还是这样想。
《性的教育》译序
2023-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