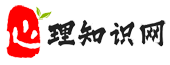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
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一页一页地越读越觉得面熟情切,不断地唤醒了半世纪来种种往事的回忆。
潘光旦先生1939年11月开始译注这本书,1941年11月竣事,足足两个年头。这两年是抗战初期,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我是1938年到昆明的,后于潘先生南下约一年,在云南大学任职,1943年前主要在云南滇池周围进行内地农村调查。后来我和潘先生分别疏散在郊外两地,见面的机会不多。我没有看到他译注此书时的工作情况。这本书译成后过了五年,到1946年四月才在重庆初版,十月在上海再版。我们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都迁居昆明城里,并且共同参与这时期的民主运动。这书在重庆初版时,潘先生和我已相偕离滇,同住在江苏浒墅关度夏。书在上海再版时,我已出国重访英伦。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不然的话,我在浒墅关整理《生育制度》的稿子时就会提到霭氏这本书了。我和这书初次见面当在1947年春季返国和潘先生同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之时。屈指计算到今年有缘与此书再见,其间已有三十九年之久。
当然,潘先生打算译注此书,我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1933~1935年,像其他在他门下的学生一样,早已从他的口头听到过,而且都盼望早日实现,因为霭氏是英国著名文豪,他的著作对于当时像我一般水平的学生读起来是相当吃力的,而且也不见得能懂。
潘先生决定译注这本书是出于对霭氏之学的倾心服膺,自称具有一种“私淑”的心理。私淑是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之意。其实,我看,霭氏之学确乎不失为潘先生毕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泉源。真是如他在该书自题诗所说的“一识相思百事蠲”。从他从事专业训练的程序上也不难看出循循诱导他进入学术园地的正是这位大师:潘先生1922年出国先人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茂大学,学生物学。1924年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他利用这两年的暑假进入各地的暑期学习班,读人类学、优生学、甚至单细胞生物学。这张课程表充分表明了他的志趣是在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为此准备结实的科学基础。他返国后在各大学讲授的课程和所有的著作也可以说百变不离“提高民族素质”这个宗。如果追问他的这个志趣来自何方,除了他爱国、爱民族之外那就不能不推到他早期所受这位私淑大师的引导了。
潘先生自称在1920年,时年二十岁*已接触到霭氏著作。那时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上学。霭氏所著的六大册《性心理学研究录》打中了这个青年人的心窍。像一颗种子落入了一块几乎是为它特地准备的沃土,一两年里就长出了新苗。他在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用霭氏之学结合了中国文献资料写出《冯小青考》的论文,也就是后来1927年在新月书店出版的《冯小青》一书的初稿。
当时敢于在这个大师面前交上这样一篇在常人眼里很可能是“离经叛道”或者至少是不太“正经”的论文,不能不说是个大胆果断的行动。更不简单的是在民国早年那个时代这位大师竟用了奖励的口吻作出“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的批语。我不知道梁氏对潘先生的赏识是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但无疑是这篇文章给了这位大师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此看出了这个后生可畏的前途。后来在另一篇潘先生上交的论文上批了下面一句话:“以子之
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澜。”
有人认为潘先生主张通才教育,而且身体力行,表明了他没有接受这一教训。我则不以为然。泛澜是指大水流出了河床,而潘先生广博洋溢的学术思想始终没有越出他自己选定的那条“强种优生”的主流。正因为不使他的才智“泛澜”,所以他断了腿还是步步踏实,在国外吸取生物科学的精华,奠定他返国后在改善民族素质的研究上发挥作用的结实基础。推溯潘先生这条学术的源头就会见到这位私淑老师霭理士对他影响之大且深了。
霭理士是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早年英国文坛上的一颗明星,曾被誉为当时“最文明的英国人。”他出生于1859年,正是达尔文《物种起源》见世之年,幼于达尔文五十岁,长于潘先生四十岁。没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久。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出版之年,也是潘先生在埋头译注本书之时。*
霭氏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学评论家,获得当时大文豪托马斯·哈代的赏识而一举成名,踏上英国的文坛。他主编《人鱼戏剧丛书》,却遭到保守势力的打击而退职。他不仅是个文艺作家,而且是个受过严格医学训练的科学家。他创议并主编《现代科学丛书》,为英国的科普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最有功于当世的还是他对性心理的研究和为性教育奠定科学基础。他以流畅多采的文笔传播严格的科学知识,开创了一代学风,遗泽后世,受人颂扬。
他一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顺当的。正如他自己在《我的生平》的序里说的:“一切著述都是一场不断的奋斗。每天早晨,凡是真正思想活跃的作者必须重新征服一切阻碍以取得表达的自由。一路上密集着由传统和假冒为善所组成的队伍,等待突击每一个散漫的过客。”他接着说,英国和一些其他国家一样,至少已有两个世纪那么长的时期,万马齐喑,不去反映与生活攸关的生动事实了。他们深怕越出了“上等人”所划下控制着人们的框框,他说:“我却不能接受这些清规戒律。”他确是出格了,出了十九世纪英国传统的所谓社会风化的格子。他被迫离开《人鱼戏剧丛书》的主编职务,他的《性心理研究录》第一辑英文版一进书店就被全部收买去毁销了,以致这部现在认为奠定性心理科学研究基础的名著还得在德国出版,初次与世人见面。霭氏最后是个胜利者,在《我的生平》序言里说:“我的一生有时像是用流血的双脚走向基督受难的圣地。凡是我的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我已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尝到了天堂里的愉快。胜于理解的宁静牢住我心。青年时所打算的一生事业在半个世纪里能得到完成,和它所给我的安慰,不能不说是超过了我梦寐所求。”
他的痛苦和他的慰藉固然是通过他个人的意志和不懈努力所获得的,但只有在他这个时代里,他所做的这一套事业才会使他有这样的折磨和报答。他生逢什么时代呢?我在上面特地在提到他的出生年月时联系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是一个最容易理解的历史界石。《世界史纲》的作者韦尔斯曾以1848年为杠杠,把十九世纪分成前后两期。在前期西方的一些先进国家的机械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已完成,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但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却还没有跟上。但是后期却有“一股强大的新的社会、宗教和政治思潮闯入了普通欧洲人的心里”。当时统治着欧洲社会思想意识的支柱是有宗教支持的“神创论”的世界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
它作为新思想的先锋突破了旧有意识形态的封锁线。达尔文把人类也纳入了其他一切生物的同一发展系统之中,也就使人类成了可以作为客观事物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出现人文主义的关键。
达尔文破了这一大关。过了三十五年,霭理士才有第一本关于两性问题的著作《男与女》问世。但是三十五年看来还是不足使科学观点在社会上得到普及,霭理士关于人类两性研究这朵玫瑰花还得用灵魂的鲜血去浇灌,直到他晚年才能松了口气,看到自己宿愿的实现。那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了,离今不到五十年。
为什么人类的两性之学如是之难产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想起了四十年前所写的《生育制度》那本书来了。在那本书里我提到人的两性行为对社会绵续和稳定上所具有的两重性。人们都容易理解人的寿命有限,不通过生殖作用和世代继替,社会不可能绵续下去。生殖作用是社会绵续的生物基础。人类是男女分体的动物,生殖作用必须通过男女的两性关系。因之,两性关系是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这是一面。另一面是两性关系也存在着破坏社会结构的潜在力量。食色性也。色是从生物基础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如果容许这种吸引力任意冲击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混乱和破坏,以致社会的分工体系无从稳定地运行。所以自从人类形成了社会,没有不运用社会的力量对人的两性行为加以严格的控制。就是说没有一个社会不立下种种规定,以限制一个人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一定范围里,对一定对象发生性行为。而且一般说来,为了维护这类社会规定对越规行为总是运用了很强烈的社会制裁。这也是社会生活里的一桩大事。
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绵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两重性。
看来,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形成了较复杂的结构,人际关系更需要稳定和巩固,上述的两重性的比重就出现了倾侧,就是着重强调人们生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而把人类两性行为封闭在狭小的范围之内,甚至把两性关系只视作生殖作用,而抹杀了男女感情的心理机能在社会生活中和社会发展上的重要性。事实上,这样的倾侧是不可能彻底做到的。两性关系根本上是有生物基础的所谓“人之大欲”。社会要把它封锁在“正规渠道”里,如果这渠道不能满足这种“大欲”,溢出渠道的行为还是不断会发生。但是更严重的是社会对这种“大欲”所采取的遏制,在强大的社会制裁之下,常使在这种社会里长成的人,在心理的正常发育上,受到了种种挫伤。其严重性在现代西方社会里已被所谓“精神分析学”所充分暴露了出来。不论对精神分析学的各种理论采取什么态度,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当前西方现代社会里,由于社会对两性关系的遏制和对性知识的封锁,精神病的治疗已成了一项热门职业。
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我没有研究,但是直到如今性知识的传播,虽则已因“计划生育”的需要已不受禁止,但是由于社会的传统影响,还是很难说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潘先生关于早年情况的描述,还适用于今日。他说,对于性的问题,“三十年前的环境里,向父母发问是不行的,向老师请教是不行的当时只有一条可以走的路就是找书看,并且还不能冠冕堂皇地
看,而必须偷看”。这里所说的书,当然不是什么“正经”的书,所以潘先生说,“至于科学的价值则可以说等于零”。可见我们的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和西方的传统社会一样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是不是和西方一样由于遏制个人性生活的正常发展也产生种种变态心理?潘先生的《冯小青》和本书的注释可以答复这个问题。更详尽的历史面貌当然还待进一步有系统的研究。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精神病症的广泛性也有待调查研究,早日开展,加以科学的核实,使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明推广性教育是重要的。
潘先生和霭理士一样相信我在上面所说的社会对两性关系的两重性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他们都反对两性关系放任自流,这是会引起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但都同时也极力反对采取遏制的手段。他们不仅看到个人在性生活上受到遏制会引起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不良影响,而且也违背强种优生之道,不利于社会发展。
潘先生认为人的性生活应当做到“发情止礼”。那就是说,发生于生物基础的“人欲”是出于自然的,必须按自然的演化规律得到发展。人为地加以禁遏不但难于贯彻,而且必然带来对身心的不良后果。最终也必然走到与强种优生相反的路上去。个人性的要求必须在不影响社会健全运行的渠道里去得到满足。这个渠道就是潘先生所说的“礼”。这里所说的“礼”并不是传统社会里用来遏制个人性生活的“礼教”,而是能使个人得到美满的性生活的社会渠道。这也就是霭理士所提倡的“恋爱的艺术。”“恋爱的艺术”并不把男女的性生活只看成是一种生物现象。人类的两性生活不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过两性之间的感情,可以丰富和美化人类生活的内容,使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升华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同时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动力。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在对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且能在群众中普及了这种科学认识,两性生活,才有条件提高到艺术的境界。这就是潘先生在本书自题诗交代的主旨:“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对性知识的封锁是使人类“瞎马盲人骑到今”。
霭理士是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对人类两性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他尽了毕生之力,披荆砍棘,终于突破了传统的愚昧所设下的重重障碍,在西方奠定了人类两性之学的基础,为社会上推广性的教育提供了科学教材。他真不愧是一个“最文明的英国人”。接住这个火把,把它传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的,就是潘先生。他在抗战岁月里,以“传经”的精神,克服一切生活上的困难,终于把这本巨著翻译成平顺易读的汉语,犹恐读者陌于中西之别,以他平时研究的成果,列举有关的中国资料来为原文注释。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他谆谆善诱的功夫。什么力量推动着他这样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的呢?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和热爱。他把一生贡献在强种优生的研究上,勤于耕种,不问收获。正是这种精神是我们国家昌盛、民族优秀的保证。
潘先生逝世转瞬间即将十年。这十年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发展最快的十年,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局面正在通过开放和改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科学与民主已成了群众性的要求。在这个时刻潘先生这本《性心理学》的译注本得到重刊可以说不是偶然的。我虽不敢说封建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凝结成的坚冰已经破冻,历来成为禁区的“两性之学”将能得到坦率和热情的接受,但我相信霭氏所说的那支“密集着由传统和假冒为善所组成的队伍”可能已
失去了过去那样巩固的阵地了。这本书的遭遇正是我国文明水平的测验。时来运转,我盼望潘先生在天之灵,会早日感觉到霭氏晚年那种宁静的自慰。
费孝通
1986年7月21日
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
2023-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