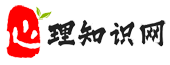①《妇女问题》(DIeFrauenfrage),1901年出版,第28页以降。
②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至十节。——译者
③同注②所引字典,“犯好”条下。
①同注③所引书,第359—361页。
制度的发展,三是此种制度所崇尚与培植的种种刚性与好勇斗狠的理想。就是武士道(Chivalry)的英雄美人的一部分的理想,名为对于女子有特别的好处,实际上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戈蒂埃(Gautier)在他那本讲武士道的巨著里,聚集了不少的材料,来证明封建的精神,好比古往今来到处的尚武精神一样,名义上间或把女子捧得天高,但是大体上在底子里总蕴蓄着鄙夷女子的臭味。我们在《蒙叨庞的瑞诺》(RenausdeMontauban)里,就读到这样的一段话:“到你的珠帘画栋的阁上去,在荫凉的地方坐下,怎样舒服,你就怎样,吃、喝、织锦、染丝,都由得你,但记住,我们的事你不用管。我们的事是拿了钢刀——斫。别作声!”假定那女人还要作声,她脸上也许就吃上一刀,随后就有血流出来。丈夫有鞭打妻子的权利,妻子犯奸,要打,女子说话冒犯了他,也要打。这些都是武士道时代的产物。但女子也并非全无权利;在十三世纪所搜罗拢来的《习惯法章》(Coutumes)里说,丈夫打妻子是可以的,但总得打得合乎情理(resnablement)。①在封建时代一个武士的眼光里,骏马与美人并重,并且骏马的价值往往在美人之上。在《麦兹的吉尔倍》(GirbersdeMetz)里,不有这样一段会话么?两个武士,一个叫加尔仁(Garin),一个叫吉尔贝(Girbert),是两个中表弟兄,他们同时骑马过一家人家的窗口。窗口正坐着一位面如桃李、肤如白玉俏美女。加尔仁说:“表哥,你瞧,好一位漂亮的女子!②吉尔贝回答说:“嘿,我的马才漂亮咧!”加尔仁说:“我还没有见过比这位白皮肤黑眼睛更教人可爱的东西。”吉尔贝又回答说:“我这匹骏马的是盖世无双。”武士的时代里,男子既这样的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武事的上面,所以男女爱悦的行为,往往只好由青年女子自己发动。高谛霭在他的书里说:“在所有法国民族的长歌(chansonsdegeste)里面,为了恋爱追逐的全都是女子,有时候亏她们的脸皮真老。”但高氏也说,这时代里妻子的操守却比较的要好。③其在英国,泊洛克(Pollock)和梅特兰(Maitland)以为在英国的条顿民族中间,女子的地位虽不高,但终身受制于男子的现象,却也始终不曾有过①。霍布豪斯(见前)也说:“自诺曼人入主英国(NormanConquest)以后,凡属未婚的女子,一到成年,便取得一切法律和公民的权利,她在法律上的人格便和三千年前的巴比伦的女子没有分别”②。但是这种对于未婚女子的种种好处,到了后来发展成熟的英国法律里,便被对于已婚女子的种种规定给抵销了,并且抵销了还不够,因为两下是很矛盾的。根据这后来的法律,已婚女子是绝不负责的一个人。除了杀害她自己的夫主的最高的罪名以外,什么行为她都不负责。霍布豪斯继续着说:“英国的妻子纵不是她的丈夫的奴隶,至少是他的子民(liegesubject),要是她把他杀了,她就犯了一个“雏形的叛逆的罪”(pettytreason),无异小国家里的一个平民对于王上的阴谋篡夺,所以比普通杀人的罪还要来得严重。丈夫在的时候,妻子是没有法子杀人的,因为她的人
①至于丈夫鞭打妻于的权利,参看注①所引霍氏书,第一册,第234页。就英国而论,一直要到查理二世许多新运动发韧的时候,才把此种权利注销。
②原文中有赌咒的语气,并引圣马利亚的神灵监誓,不妨译作“向圣母保证”.但译文中省略。——译者
③《武士道》(LaChevalerie),第236—238、348—350页。
①《英国法律史》(HistoryofEnglishLaw),第二册,第437页。
②同前霍氏书,第一册,第224页。
格从结婚的日子起便变做他的人格的一部分;她要有什么犯罪的行为,那责任便十有八九要归到丈夫身上(英国丈夫的所以有鞭打妻子之权,原因在此):同时丈夫也不能和妻子订什么契约,因为和她订,便无异和自己订,那是不通的。勃拉克士东(Blackstone)说:“在婚姻的时期以内,女子本身的人格和法人的地位是搁置一边。不生效力的,至少是和丈夫的夹在一起、变做一块,她的一切工作,是在他的羽翼、庇荫、与保护之下做的。英国法律上的女性”,勃氏又说,“真是一个天之骄子呀!”霍氏解释英国法律的意义,也说:“女子的力量就是她的软弱。她以退为进、以败制胜。她的温柔要受爱护,免得被世间的扰攘给摧残了,她的芬芳馥郁,要妥为保存,不要使与外边的飞扬的烟灰尘土同流合污。因此,她就不能没有一个保镳和护卫的人了。”
在中古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妻子在夫家的地位和上文所说的很是一样。丈夫是她的绝对的主人,是她的头脑和灵魂,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细小的东西”怎能不用“全副精神来爱他顺他”呢?反过来,她是丈夫的第一名的仆人,是最大的儿女,是妻子,是子民,她向他寄家书的时候,末后总要写“你的谦卑的、顺从的女儿和朋友某”。史学家拉克莱维尔(DeMauldelaClaviere),在他那本《文艺复兴时代的妇女》(FemmesdelaRenaissance)里,在这一点上搜集了不少的证据;但他也说,丈夫虽享受这种崇高的地位,抱怨着婚姻生活的苦难的一方,还大都是他,而不是他的妻子。
法律和习惯一向都假定女子多少得受男子的保护。在后世最较开明的对于女性的理想里,不论其为封建时代的或封建时代以还的,都还可以觉察到此种假定的力量。这样一个假定当然也暗示女子不及男子,女子不能和男子讲平等;但是,在扰攘的封建社会里,这不平等倒也对女子有利。在那时候,男子的刚性的力是左右生活的一大因素,所以为女子的安全计,他应该取得这力的一部分,做她的帮衬。这样一个看法,也自很通情达理,所以到了后来,武力的效用虽渐减少,而此种看法却依然保留不替。在伊利沙白女皇时代的英国,一个女子还总得有个主儿;伊利沙白自己便是一个女子,有聪明,有才干,能够治国家,建功绩,却并没有主儿;这不是很客观的告诉当时的女性的民众,没有主儿也不要紧么?但她们并不理会,还是觉得主儿是少不得的。再后,到了第十八世纪,那样一个有眼光的道德家,像夏夫茨伯瑞(Shaftsbury),在他那本《品格)(Characteristics)一书里,也还不免把已婚女子的外遇看作侵犯别人财产的罪人。要是当时最卓越的思想家还不免有此种见地,那末,在同一个世纪里,甚至于到了再下一个世纪里,一般比较不学无术的人,实行此种见地,把女子公开的买卖,恬然不知羞耻,——也就不足为奇了。
希拉德在他的《实用辞典)里说①,起初的时候,买一个妻子是买她整个的人,不止买保护她的权利。这原来的观念似也许在英国流行得比较长久,因为它僻处西陲,和迤东的文化中心比较远的缘故。在第十一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VII)盼望兰佛朗克(Lanfranc)禁止苏格兰和英伦一带的卖妻的行为。②但是在偏僻的乡区里,此种行为后来到底没有能禁绝。
这种买卖的行为在伦敦都还有。在一七六七年的(常年登记册》(Annual
①schrader,Reallexicon,“买妻”条下。
②见拜克《英国犯罪史》(Pike,HistoTyofcrimeinEnglend)第一册,第99页。
Register)里(第99页),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大约三星期以前,玛利勒朋地方的一个泥水工人把曾经和他同居过好几年的女人,卖给一个同行,代价是一个几尼③的四分之一和一加仑啤酒。那工人随后就把那妇人带走了,也是她的运气正要转了,正在那时候,在德文郡(Devonshire)的一个舅父死了,遗留给她二百金镑,还有一套碟子。他俩在上礼拜五也就正式结了婚。
俘克士牧师(Rev.J.EdwardVaux)在他的书里叙述两件买妻子的事,都在十九世纪以内,并且都是在闹市上成交的。一例是原来的丈夫,得了妻子的完全的同意,用一根绳子拴套在她的脖子上,把她领到市场上,后来卖给另一个男子,得了半个克朗的代价(二先令半),那妻子就跟了这男子到他在三十里以外的家。其他一例的两造之一是一个客店的老板,他是承买的,代价是一坛麦酒,有两加伦重④。
女子是财产的一种,或形同财产,在这里是很明显的。但这种观念所及甚远,即在今日,也还在许多陈旧的法律的条文里可以看出来。例如一个男子和一个处女发生了性交,随后又把她遗弃,一经起诉,那男子就得向女子纳赔偿的金额①。原来处女经性交以后,她的“名誉”便受了损失,她的市价就不免跌落,恰恰好比故衣店里的衣件,即使以前只穿过一次,也总是旧的,不能再卖新的价钱。但在男子,无论他和女子发生过多少次的性交,他就决不承认他的个人的价值会有什么减少。
因为这种不平等的事实,便有人主张取消所谓“体质上的处女性”。一位德国的女作家在她的作品②里,以为一个女子的保障,决不在小小的一片膜,而在一个真挚的、机警的灵魂;因此,她就主张在童年的时候,就施手术把处女膜割去。我们一向确乎是太把处女膜看重了,唯其看得太重,我们才有虚伪的女性的“名誉”观念,和不健全的女性的贞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