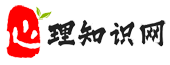窒息自我,机械趋同:尽管丁的真自我规避到自身之内来打压身体化自我,但是他还是无法否定现实世界的存在。而假自我要想存活,就得窒息自我的真实欲望来与现实世界建立正常的关系。为了迎合新英格兰人们的期望,丁完全根据清教规范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以神的标准要求自己,将自己打造成众人所期待的模样,这使得假自我深受新英格兰人的尊敬与赞美。然而,他的身体化自我越是在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成功地扮演一个牧师的角色,在其真自我看来,这种行为越显得是可耻的和可笑的伪装。这样,他与外部世界的裂缝不但没有弥合反而破裂得更大了:教民们认可的是他作为圣洁的牧师的存在,而丁认可的却自己是作为罪人的存在。双方期待中的身份认同差异使得丁自我与身体之间的分裂被扭曲和放大,更受直面或逃避两种选择的撕扯。因而人们越是赞美他,他越痛苦。面对新英格兰人民的无上赞美,丁却觉得自己“是一团污秽,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3],可见丁的牧师身份只会使自我陷入更深的矛盾。 那么丁为什么在犯了罪后继续做了长达七年上帝和俗世的中介呢?这只是丁身体化自我为了适应现实世界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他真实的愿望,即真自我思考的产物。丁一旦以本真面目示人,他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因此,迎合他人的期望将真实的自我埋葬于牧师这一社会角色之中,即通过“机械趋同”,是丁为了生存的一种无奈手段。丁七年牧师身份的正常运转正是通过越来越绝望地打压真实自我,在他人错误的身份认同中依次获得模糊而脆弱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来加以维持的。在牧师这一“保护色”身份的遮掩下“‘我’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5]。但牧师身份这时已经“失却了人的本性而‘被’神圣化,生活在人间社会却不能有人的情感和自由的俗世生活,在神圣光环的辉映下失去了真实的自我而沦为一种象征” [6]在众人的眼中,与其说丁是一位上帝在俗世的代言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宗教精神的传声筒,一个社会符号。同时,丁也被置于极端不安的状态,因为他被迫与别人趋同,屈从于虚假的神圣性,献身于上帝来进行自我肯定,所以得到的只是一种虚伪的身份认同,并最终会导致自我的个性和完整性的丧失。
窒息自我,机械趋同
2023-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