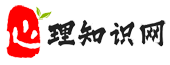窃恋和虐恋不但在名词上相仿。在性质上也有联带关系。窃恋可以说是建筑在更广泛的虐恋的基础上的;虐恋中的性情绪的联系物是痛楚,窃恋中的性情绪的联系物是一种提心吊胆的心理,而提心吊胆的心理也未始不是痛楚的一种。③这样一个看法以前有不少观察家也提到过,但都不很清楚,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年,经法国的一部分精神病学者[例如德普伊(Depouy)在1905年]把若干窃恋的例子明确地叙述以后,这看法才算成立,而窃恋的性的,含义才完全显露。这些精神病学者告诉我们,窃恋的心理过程实际上就是积欲与解欲的性的过程,不过经过一度象征性的变换之后,就成一种偏执性的冲动,而此种冲动,在活跃之际,也必有一番抵拒挣扎,活跃的结果,则为一件很无价值的东西的窃取,往往是一块绸缎的零头或其他类似的物料,除了藉以取得可能的性兴奋而外,可以说全无用处。内心的抵拒挣扎相当于积欲的过程,我们知道普通积欲的过程里,本就有不少抵拒挣扎的成分;而窃取的最后手段则相当于解欲的过程,我们也知道,有的窃恋的例子,在窃取成功之顷,真会发生解欲的作用而取得情绪上的宣泄。至于那偷到的东西,到此不是藏放一边,便是完全抛弃,真是捐同秋扇了。
②见狄氏与比姆女士合著的《一千件婚姻的研究》一书。
③所指当然是各式生育节制的行为。晚近论生育节制的道德的人,大抵承认只有在两种情形下节育是合情
理的,一是母亲有病态,不宜任生育之劳;二是男女的、一方或双方有违反民族卫生或优生原则的遗传品
性。
窃恋的人大抵是一个女子,并且往往是有相当身家的女子,更可见她的所以偷窃,目的决不在东西,而是别有作用。这样一个女子对于偷窃行为的性的作用也许并不了解,并不自觉,即使自觉也不会自动地承认。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窃恋事实上并不是“窃狂”的一种,两者在以前虽往往相混,现在我们却看得很清楚了。“窃狂”在理论上是认为没有动机的,也是不可抗拒的;而窃恋则自有其确切的动机,初不论此动机的自觉与否——此动机并非愉窃他人物件,已不待言;同时,偷窃的行为也不能说不可抗拒,因为当事人总是筹之已熟,见有机会来到,环境适宜,便尔很快地下手。又大凡窃恋的人,神经上虽十九有些变态,精神上却不一定有严重的病态。窃恋决不是一种精神病,因此,也就不能和目前事实上已成过去的“窃狂”相提并论,而应完全归纳到性心理学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妨把窃恋看作性爱的物恋现象的比较有病态的一种。④窃恋而外,还有性冲动与偷窃行为的混合现象,这些虽和窃恋不无联带关系,却不应与我们所了解的窃恋混为一谈,并且这些现象的发生,事实上也比窃恋为少。这些现象之一,斯特克尔(Stekel)在1908年曾经特别叙述过。:这现象里的偷窃行为是不属于性爱性质的,易言之,偷窈并不成为获取性满足的一个方法,所窃取到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恋物,而是任何表面上可以供给性的兴趣或性的暗示的物件。窃取这样一件东西,当事人,大抵也是女子,算是聊胜于无地得到了一些性的满足,这种女子大都因丈夫阳事不举而平时情绪上感受着多量的抑制的;一种有性暗示的事物的窃取对她多少有望梅止渴的用处,此外别无意义。斯氏用这个现象来解释一切“窃狂”的例子,不过假若我们不再承认“窃狂”的存在,这解释也就根本用不着了。至于这现象既不是物恋又不是窃恋,是显而易见无烦多事解释的。
性的情绪与偷窃行为的另一混合的现象,曾经美国犯罪心理学家希利叙述过,并且还有过实例的证明。以春机发陈年龄前后的青年男女,一面受了性的诱惑,一面又深觉此种诱惑的罪大恶极,不敢自暴自弃,于是转而从事于罪孽比较轻微的愉窃行为。⑤这现象背后的心理过程可以说恰好是窃恋心理过程的反面,因为一样是实行偷窃。在窃恋,其目的是在性欲的真实的满足或象征的满足,而希氏所述的现象,则为此种满足的闪避。
④霭氏原注:所谓物恋现象里的“恋物”一名词,原先只适用于衣履一类的物件。但自1888年法人比内
那本典范的作品出来以后,这种狭隘的限制是早经取消的了。
:霭氏所指当是比内的《实验心理研究录》一书;比氏在这本作品里认为全部性的选择是一种物恋现象,
他说:“正常的恋爱是一套复杂的物恋现象的结果。”
以前西洋人所称的“邪孽”,比内等一部分性心理学家所称的“物恋”霭氏自己在三四十年前所惯用的”性爱的象征现象”,一部分比较后起的性心理学者所说的“性欲出位”,以及瞩氏在本书里提出的“性的
歧变”,所指的只是一种现象。
⑤见琼氏《精神分析论文集)中《象征现象的学说)一文。
⑥枯杨恋的译名原本《周易·大过》,《大过》上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
其士夫。”近江南俗称女于五十岁以后月经绝而复至为“老树开花”,以枯杨代表老人,词较雅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