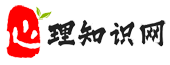超个人心理学的人生意义论:超个人心理学十分重视人生的意义或价值,并认为对人生意义的研究、探讨是心理学无可逃避的责任。
人本主义心理学坚持人生的意义并认为心理学应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例如,马斯洛就曾多次批评过传统心理学的“脱离价值、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式”,认为心理学如不涉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就不会为培养真正健康的人格(社会成员)发挥作用[1](p171)。超个人心理学坚持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一主张,并加以发展。这种发展使人本主义心理学所理解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变得更为广大、永恒和崇高。正如李安德在其《超个人心理学:心理学的新典范》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多亏人本心理学的努力才把价值与意义重新引进心理学研究范围,超个人心理学不仅肯定这一发展趋势,还把价值与意义放在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此外,超个人心理学特别强调超越个人兴趣的价值与意义,并且打破传统的忌讳,研究终极的价值与意义[2](p204)。
超个人心理学实现自己的这一主张的第一步是对当前流行的个人主义的自我观念与相应的价值观念的批判,认为社会上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所引起的。李安德特别认真地列举了前后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的七位着名的心理学家对流行的个人主义价值和意义观点的严厉批评。这七位心理学家包括有:詹姆斯、墨菲、斯密斯、阿尔波特、罗杰斯、马斯洛和堪拜尔(Campbell)。这些人大都批判了从个人主义来理解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错误和危害,主张从超脱个体的更广阔的范围来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这些人并非都是超个人心理学的同道者和支持者[2](p319-324)。
应该说,到这一步为止,超个人心理学家们的主张、立论都是正确的和无可厚非的。但在其努力的下一步即如何扩展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上却发生了重大的问题。
从其具体内容讲,所谓人生意义不外是指人的生活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和影响,一般说是指其积极方面的影响而言的。从此就可以分析出所谓意义的成分或构成要件。其中除了这种结果和影响本身以外,还有两个方面的要件,即这一影响的始发者或制造者以及这一影响的承受者和评价者。由于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因此,影响和意义的发生常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但它却不以有这种意义的制造的目的者为限,因为无此目的的活动依然有其意义存在。意义的存在还依赖于这种影响的承受与评价者的存在。影响而无其承受者自然不成其为意义,其理极明。而如果没有评价者,没有对这种影响的觉察、审视和评价,也不会成其为意义。因为对于没有觉察、评价能力的东西来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但却是谈不上意义的。另外,还需要指出,上述的影响虽属客观存在之物,但随其制造者与承受者及其间关系的变化,它的作用也会有极大的不同。
正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人生意义的差异。而在这三者之中,可以认为,正是影响的制造者与承受者两个方面的差异对人生意义的差异有更大的影响。例如,对影响和意义的承受者所理解和认定的范围,就对人生意义的大小和时间的持久性有重大的影响:当把影响和意义的承受者只设想或限制于其制造者个人本身的时候,人生的意义就会是极其狭小的或在时间上极其短暂的,如超个人心理学家所批判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或我国历史上杨朱派所主张的那样;而当把它扩展到他人、制造者所属的群体乃至人类全体时,人生的意义就会更为广大并在所经历的时间上大为延长,如果进一步把它理解为和推广到超出人类之上的某种精神实体时,则不仅人生的意义会得到无限扩大,在时间上也成为永恒的东西了。而从影响和意义的制造者一方来看,如果把它仅归结为个体的某种偶然的行为,则其意义就会显得平凡而不足称道;而如果能使之归属为人类的某种普遍本性(如弗兰克尔的“意义意志”),它就会显得更为高尚和圣洁;而如果能把这种制造意义或影响的行为与某种超越人类的精神力量联系起来作为其作用的结果,则这种行为及其所体现的人生意义,就将成为无上神圣的了。
超个人心理学的倡导者们就是从这种思路出发来行事的。超个人心理学者提出要求人类“从小我归向大我”。他们认为,除了我们通常所体验到的自我之外,还有一个超乎个体之上的高层的我。它也可以被称之为“大我”、“宇宙我”或“普遍我”,它是我们自己以外的存在的“全体”。这种“宇宙我”或“大我”与我们的个体自我同样具有有意识的性质,具有个体我所具有的那些优美的品性,只不过它具有更为广大、根本和原初的性质。两者相比,个体之我不过只是它在意识之中的残缺不全的倒影,个体我的一切思想行为都是在它的指令或感召之下发生和实现的[2](p317-318)。经过这样的一番提升工夫,个体之我也就成了这种具有意识性的宇宙大我的一部分,个体我对影响和意义的创造行为与承受评价等,都成了这种无所不包的永存的大我的意志和愿望的表现,因而人生的意义也就可以提升到无限宽广、永恒和至高神圣的境界了。
这种作法是有效的,但也给超个人心理学带来损失,使之受到理所应得的责难。因为,作为与宇宙同在的超人类的精神的、意识的本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这种主张的提出是与整个科学发展所积累的事实相冲突的。同时,这种主张也使超个人心理学沦入与宗教为伴的境地。虽然超个人心理学家不断申言自己与宗教的区别,强调相信来世和再生的只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辩解只能是徒劳的。因为,承认一个超越整个人类之上的有意识的本体(如詹姆斯所称为的宇宙意识流)的存在,这个有意识的本体不是宗教中的神又是什么?教人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永恒的有意识的力量的存在及其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支配作用,其社会作用与一般的宗教宣传有什么差别?因此,对某些超个人心理学家来说,即使他们不公开宣扬宗教中的人格神的作用,也不能使他们摆脱其为宗教的亲密伙伴的尴尬局面。这样,为了提升人生意义的广阔性、永恒性和神圣性,而不得不放弃对其现实性上的要求。
在当代西方着名的心理学家中,弗兰克尔要算是最重视对人生意义的研究了。因此,他的名字和言论也就极常为超个人心理学的有关的着作所引用。但是,弗兰克尔与超个人心理学之间是有同又有异。弗兰克尔与超个人心理学家同样重视人生意义的研究并将它置于自己心理学理论的中心位置上,这一点使人们有理由把他们同样地称为意义心理学家;但是,他们关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说明却有根本的不同。弗兰克尔也将影响和意义的承受者从其创制者的个人加以扩延,但他所扩及的只是他人、个人所属的人群以至全人类为止,并未扩展到一个超人类、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在人的有意义的思想和行为的内在依据方面,他也只是达到了人类本身所普遍具有的“意义意志”,并未提到其背后的超人类超自然的宇宙精神实体。而如果一切都还停留在“全人类”本身,就不可能有超个人心理的被推出并加以宣扬和推崇,因为作为整体的“全人类”是不能离开人类的个体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和可能引申出超个人,超出个体的脑,身体和心理的[3](p18、20-21、220)。从这些看来,弗兰克尔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超个人心理学家,而频频地引用弗兰克尔,也终将无助于超个人心理学摆脱其理论上的真正困境。
超个人心理学的人生意义论
202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