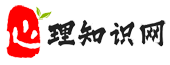把内心精神活动变为言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联想过程,而是极其复杂的心理操作过程。
文学艺术家常常会在语言的运用上感受到辞难达意的莫大痛苦。语言要表现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欲求、体验、憧憬以及种种微妙独特的情绪。
而这些属于个体独特体验中的内容,一旦被加工处理为规范化的语言后,便失去了其固有的生动、丰富、具体、鲜活的魅力。康德就反复讲:语言永远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审美意象。
而文学注定要用语言来表达审美中这种“不可言传”的东西,于是文学家便被置放到一个自相矛盾的困窘之中,文学家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起来。正如法国诗人瓦莱里说的:“在这些创造诗的世界并使它再现、使它丰富的手段中,最古老、也许是最有价值然而最复杂、最难使用的一种,是语言。”由于文学语言要求作家必须同时具备现代文明人的高度文化意识和原始人质朴的感受力,成年人的知识水准和儿童的本能的活力,就必然产生语言痛苦。因此诗人纳德松说:“世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