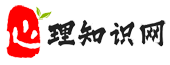举一个时常发生的简单的例子罢。一个青年男子或青年女子,事前既不向家人亲戚朋友说明,临事又不听任何旁人的劝告,突如其来地宣告行将和某某人结婚;不过这样一桩婚事,即使表面上并不违反什么优生的原则,而实际上从别的立场看,是绝对人地不相宜的。也许第三者看不过去,总希望这样一个恶姻缘可以打消,于是便向医师请教,并且有时还指望他明白地宣告,说明那轻率从事的对方实在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对方精神上究属健全与否,是应该仔细探讨的一个问题,不过,就大多数的例子而论,这是一个迹近罗织罪名的说法,那所谓轻率从事的对方或许在遗传上有一些轻微的神经变态的倾向,但此种变态,即使可以叫做变态,在分量上实在是很轻微而并不超越寻常生理的限度,因此,单单把医师找来而凭他的片言只语,是不足以断定的。莎翁剧本里所描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andJuliet)一类的爱侣,因为不胜一时兴奋之故,把反对他们结合的社会障碍完全置之度外,这是有的,但他们并不疯狂,除非是我们从文学的立场接受勃尔登在《愁的解剖》(AnatomyofMelancholy)一书里反复申论的说法,认为在一切恋爱状态中的人是疯狂的。就大多数的例子而论,我们所碰见的决不是两个疯狂的人,而是两个还没有从“狂风骤雨”③里钻出来的青年;新发展
②西人称尸恋者为吸血鬼或夜叉,教我们想起关于唐将哥舒翰的一段故事。哥舒翰未达时,有爱妾裴六娘
死,“翰甚悼之,风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殡于堂奥,既无他室,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穗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
也,长丈许,著豹皮褌,锯牙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便升阶入殡所。异衬于月中,破而取其尸,麋割
肢体,环望共食之,血流于庭,衣服狼藉”(详见唐陈劭(通幽记)及段成式《夜叉传》。)这故事
中的夜又极像西洋人的吸血鬼,不过尸恋的倾向实际上和夜叉不相干,而和哥舒翰则不无关系,哥舒翰见
的不是像境,便是梦境,并且是有尸恋色彩的梦境;未来将以杀人流血为能事为专业的人有这样一个梦境,也是情理内可有的事。
③清羊朱翁(耳邮)(卷四)亦载有富有代表性的一个尸恋的例子:”奚呆子,鄂人也,以樵苏为业,贫未有妻;然性喜淫,遇妇女问价,贱售之,不与论所直;故市人呼曰‘奚呆子”。市有某翁青,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见而艳之,每日束薪,卖之其门。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瘗处,乘夜发冢,负尸归,与之媾焉。翌日,键户出采薪,而遗火于室,烟出自窄,邻人排闼入,扑灭之;顾见床有卧者发其衾,则一裸妇,
的性爱的生活原是这番风雨的一部分,当其突然来临的时候,势必至于产生一种生理上的惊扰与此种惊扰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失其平衡。一刹那风息雨止,生理的惊扰既消,精神的平衡自然恢复,并且更不至于发生第二次。
再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行为正直而操守纯洁的青年男子,或因一时的好奇,或偶听朋友的怂恿,或完全因偶然巧合,认识了一个妓女,情投意合,竟想和她结婚,他的动机是极理想的,他以为妓女是俗人眼里最下贱的东西,既受人糟蹋于前,又永远得不到翻身于后,他这一来,就可以把她搭救出来,永离苦海,岂不是功德无量;至少这是他当时自觉的动机,在他比较不自觉的心理里,一种正在暗中摸索的性的冲动固然也未尝不存在,不过在那时是不免被搭救的理想所隐蔽而看不大出的。见和妓女结婚,在原则上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事实上结果美满的例子也未尝没有,不过在男子方面总得是个成熟而有经验的人,并且在成婚之前也一定有过一番谨慎的选择。若在一个初出茅庐的男子,天真一片,再加上理想所唤起的一般热情,莽撞做去,结果大概是不会圆满的。吕我们碰到这种例子,最好的方法是暂时取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然后相机劝止。直接与强烈的禁遏手段不但不行,并且适足以煽动他的热情,使大错的铸成更不免急转直下。虚与委蛇的用意是让他把婚事延缓下来,在这延缓的期间,就可以设法教他对所爱的人有一番静心观察的机会,结果,他对于对方所估的价值也许会降下来,而和亲戚朋友所估的相差不远。到那时,这样一桩婚事便不打消而自打消了。
再假如一个青年女子,一时为情感所驱,想草率地和人家成婚,做家长或监护人的往往可以想法使她改换一个环境,让新的兴趣和新的友谊取而代之。有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是屡见不鲜的)一个青年女子,一时意兴所至,想和一个社会阶级比她自己低的男子结婚。无论我们对于阶级的观念怎样不重视,这样一桩婚事是应当竭力加以反对的,因为它很不容易有美满的结果,而当事的女子,如果能悬崖勒马,自己也决不追悔这马是不应当勒的。近年小说里的恰特里夫人虽一时爱上了一个农家子弟,但若真要嫁给他做他的妻子,未来的生活是决不会幸福的。部这一类拿一见倾心做根据
迫视之,死人也,乃大惊;有识者曰:‘此某翁女也。’翁闻奔赴,验之,信,闻于官,论如律。异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叹宋孝武帝为殷淑仪作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尚非异事。”见近乎尸恋或夹杂有其他动机的尸交行为略引于后:
吕后陵,污辱其尸,有致死者(《通鉴》)。“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
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
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唐
戴君孚《广异记》)。“宋嘉熙间,周密近属赵某宰宜兴。宜兴前某令女有殊色,及笄而夭,藁葬县斋前
红梅树下,赵某‘遂命发之颜色如生,虽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直国色也;赵见之为之惘然心醉;异
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柔和,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夕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惙然,疲苶不可治
文书,其家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亦云异矣。’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
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旧目击,始知其说不妄。”(宋周密《齐东野语》。)
安徽抚院高,讳承爵,旗员,罢官后,一爱女死,殡于通州别业。守庄奴知其殓厚,盗启之,见女貌如生,
将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脱不得,抱滚二十五里,遇巡员获之,论碟,七日旨下。女今东浙备兵
高其佩之妹也。”(清景星构《山斋客谭》。)尸体会不会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高氏父子都是清代名
臣,其佩且以指画擅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部中有张泌《尸媚传》一种,所述多为女鬼蛊惑生人之事,姑不论其事之可能与否,要与尸恋现象截然二
的造次的结合往往要产生一系列悲惨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在成婚之前,能设法加以阻碍,这种设法总是合理的;固然我们也承认在“远亲远亲”或“近看一面麻,远看一朵花”的说法下,④障碍越多,在恋爱状态中的青年越是一往情深,追求得越用力,越不甘放弃,即使障碍发生效力,使一段姻缘功败垂成,在当事人也许会引为终身的一大憾事。英国小说大家狄更斯(Dickens)的经验是很多名望赶不上他的人同样身受过的。狄氏早年曾经爱上一个女子,但终于被她拒绝,没有缔结姻缘。后来这女子在狄氏的想象中成为十全十美的女性典型,他的作品里的女主角,也无形中拿她做了蓝本,①但最后双方再度有机会见面时,狄氏终于不免大失所望,嗒然丧气。
婚姻也有许多我们局外人的注意所达不到的特殊的疑难问题。但看不到,并不就证明没有问题。男女两人之间,不发生婚姻之议则已,否则总有一些要解决的问题的,问题发生的方面尽管很不一致,但其为问题则一,而这一类的问题之中,总有一部分会请教到医师手里,近年以来,请教人的更一天多似一天,而所请教的问题的方面也一天比一天增加了。对这一类特殊一些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略微提到,一则为本书的范围所限,再则要解决这类问题,我们不容易有什么固定不移和到处可用的简单的答案。每一桩婚事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单独的解答,也许对甲是最有利的解答对乙却说不定是最有害的。也许将来全世界的各大都市里我们都可以有一种婚姻的咨询机关,专门帮助已婚与将婚的男女就婚姻问题的各方面寻求答案[已成立的柏林性学院(sexualInstituteofBerlin)可以看作这种机关的一个前驱]。
这类的问题包括年龄、个人的健康与家世的健康或遗传、婚前的体格检查、对于婚姻生活的准备与准备到何种程度、生育的展缓与节制,特别是夫妇在身心两方面可能融洽的程度,因为这种程度的深浅和婚姻幸福的大小往往大有关系。
婚姻的年龄问题就是对待迟婚早婚的问题。究竟迟早到什么程度,才对夫妇的幸福以及健全子女的产生最为有利,是一个意见还相当纷歧的问题。就目前论,这方面的资料数量上既嫌太少,范围上也不够宽广,使我们难以做出一些可以适用于多数人的答案。在美国费城,哈特和希尔兹(Shields)两氏,根据法院里婚姻关系专庭上所处理的案件和每一对夫妇因勃豁而构讼的次数,来衡量年龄与婚姻生活美满程度的关系,发见早婚是不相宜的,而同时另一位费城的作家,柏特森(Patterson)在这方面的研究发见,在20岁以下缔结的婚姻中发生的龃龉并不比20岁以上缔结的婚姻中明显得更多。狄更生和比姆女士合作的调查里,发见凡属可以认为婚姻生活满意的(即双方能彼此适应而无不足之憾)妻子的平均婚年比全部调查里的平均婚年要大几岁,而在考虑到婚后同居生活的长短和后来分居或离婚的关系时,又发
事,不得混为一谈。
④除上文所已引用的外,下列诸种作品也可供一般的参考:霍尔:《恐惧的研究》,载《美国心理学杂志》,
1897年与1899年。布赖恩:《尸恋》.载《心理科学杂志》,1875年1月号。
①我国生理旧话说,女子七岁生齿,二六十四岁经至,七七四十九岁经绝;虽近刻画,但“经绝”一词,
颇可沿用;英文名词是menopause,或clinlacteric,或changeoflife。
②有一位极有地位与声誉的朋友告诉泽者,他的一位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哥哥在五十岁以前是一个
道学先生,主张一生不二色,对亲戚朋友中有娶妾狎娼的人,一向取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五十岁以后,忽
然把家里的使女勾引成奸,并且还有了孩子!
见婚年最早的人中,此种同居的期限倒也并不是最短的。孔成婚迟一些的女子当然比较明白自己生活里最需要的是什么,而比较能有一些健全的主张,这固然是好处;但同时这种人的心理习惯大抵已趋固定,而在身体方面,也说不定已经有一些小毛病,这种习惯与毛病的存在对婚后夫妇间的顺适总要引起不少的困难;反过来,早婚的女子不但在心理方面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并且体格方面也比较健全,性交既不感困难,生育亦易于应付;这种比较,在一般人还不很了解,但事实确乎如此。不过实际上,问题并不端在年龄的大小,而也和性格、智力及经验有关;单就年龄而论,目前的平均婚年也许是已经够高的了,并且往往是太高。近年来在婚姻问题的作家里,伯格杜弗尔(Rurgdorfer)竭力主张早婚,同时哈根(Hagen)和克里斯欣的结论是,从优生学的立场,男子婚年应为25,而女子则在25以前,假如这样提早以后,不免遭遇种种困难,这种困难,无论多大,应该用最大的勇气来克服,不应规避退缩。在德国,男子的平均婚年是29,女子的是25,不过在数世纪以前,男子的是在19岁以下,女子的是在15岁以下,相差得真是很多了。
无论在什么年龄结婚,男女双方,为未来夫妇的关系和子女的生育设想,都应当有一度周密的医学检查;这一层不但有利而值得做,就道德的立场说,也是义不容辞的。检查的手续并且要做得早,在婚约发表以前,在许多亲友知道以前,就应当做。当然,检查的工作也必须包括女子的妇科检查和男子的生殖与尿道检查。有人更主张;检查后必须有证书,而证书的有无应当成为婚约成败的第一个条件;所以在行将结婚的人应当被强迫接受检查而出示他或她的受检证书;这种主张,在有的地方,已经有实现的倾向。中不过这种检查的关系实在是大多了,即专为未来夫妇的幸福着想,而不参考到本节范围以外的种种优生学的需要,行将结婚的男女也是应当照做而愿意照做的,初不待外界的强制。婚姻还有另一种准备工作,其意义的重要更要在医学检查之上,而必须双方当事人在私底下自己做的。这种准备工作是性知识和性感觉的自我检查,婚姻关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是性的关系,在发生这种极亲密的关系以前,双方对于自己和对方行将发生这种关系的条件,应当
孔子在《论语·季氏)里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中国文献里关于年龄的个别心理的观察,无疑这是最早的
一种了;此种观察的大体准确,也是不容怀疑的。本节的讨论当然是属于第三个阶段,而霭氏的这几句
话又不啻是“戒之在得”一语的注脚。不过以前的人似乎不大知道,在“老之将至”的阶段,也未尝没
有一个“血气不定”的时期。血气既衰而又不定,“色”的刺激钎于外.而“得”的反应迫于内,于是本
节所说的一种歧变现象便势所难免了。
中国人到此年龄,男的喜欢收干女儿,女的喜欢收于儿子;尤以男的收子女儿的倾向为特别显著,几乎成
为一种风气。仅仅收干女儿还算是俗不伤雅的。等而下之就是纳妾、蓄婢、呷娼、捧坤角一类的行为了。
风流自赏的文人,到此特别喜欢收女弟子,例如清代的袁枚(子才),也属于这一类现象。诸如此类的行
为,霭氏这一段的讨论便是一个最好的解释。
中国以前在妾制流行的时代,这种能自制的人自所在而有。第一流,不置姬妾;这是不多的,但有。第二流是纳妾的,但遵守一些传统的规矩,例如四十无子始娶妾,或不娶旧家女为妾之类。第三流是虽有姬侍,
却备而不用,甚至到了可以遣嫁的年龄,便尔放出择配。这三种人,算都是有品德的
基(墨庄漫录)说:“李资政邦直,有与韩魏公书云:’前书戏间玉梳金蓖者,侍白发翁,几欲淡死矣’
玉梳金篦,盖邦直之恃姬也。人或问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欲所谓和尚置梳蓖也。’又有与魏公书云:’
旧日梳篦固无恙,亦尚增添二三人,更似和尚撮头带子云。’”这可以算第三流的一个例子。极是难得。
有一个比较明白的认识。他们应当自问,对于自己和对方身体的构造和生理,以及彼此对于性题目的情绪的反应,已经有充分的了解没有。就一向的情形而言,狄更生和比姆女士在他们的研究里所说到的一点是很寻常的,就是“少不更事的未来的新郎觉得对方是‘太神圣得’不可侵犯了,因此,对于她内部的结构,不便作什么探索的尝试;在未来的新娘方面也把自己当作是一棵树,那么一根实心的木头。这种男女对于生理与解剖的知识比起古代的波斯人来,并不高明得多少。”他们特别应当自问一下,他们对于婚姻之爱或床第之爱的观感究属如何。我们知道有的夫妇深怕对方触摸到自己的私处和其他平时不大呈露的发欲带部分;有的夫妇从来没有在浴室里碰过头,不是他怕见她,就是她怕见他。在这种情形下,身体上的开诚布公,和盘托出,既谈不到,要取得精神上的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更不必说了;这样,试问还有真正的婚姻结合可言么?戴维斯女医师发见,凡属婚前的准备,不论在哪方面都比较充分的女子,比起没有准备的来,其婚后生活的比较圆满,在百分数上要多占许多。
这种相互的认识当然不限于性的方面。婚姻关系中,性的关系既属中心,但并不是惟一的关系。我们知道有许多婚姻的例子里,真正的性关系始终不曾有过,但因双方有十足的性格上的体认,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不圆满。许多婚姻的研究都认为性情投合是婚姻幸福的最大的钥匙。棋两个人的性情,单独看,也许是很不差的,但放在一起,就合不起来,所以必须在婚前加以认识;留待婚后再加以体验是不妥当的。最好在结婚以前,双方就能有较长期住在一起的机会,这同住的环境必须能供给种种寻常必须解决的问题以至特别不容易解决的难题,让双方共同设法应付;如此,双方才可以观察到彼此对自己、对第三者以及对一般事物的反应的方法;我特别提到对第三者以及一般事物的反应,因为只看双方彼此间的反应是不够的,这些,在婚前婚后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天主教里的修士和修女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见习及格才可以正式做修士和修女,我认为婚姻也应当有一个见习的阶段,见习有成,才许在婚姻祭坛前立下正式的誓约。这种见习功夫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包括不包括性的交合在内,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所谓性情的投合,不一定指性情
棋(郎潜纪闻)(卷二)说:“方格敏公观承子襄勤公维甸,两世为尚书直隶总督,皆有名绩。格敏五十
未有子,抚浙时使人于江宁买一女于,公女兄弟送至杭州,将筮日纳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见诗册有故
友名,询之,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时与此君联诗社,安得纳其孙女乎?’还其家,资助嫁
之。公年六十一矣,吴大夫人旋生子,即襄勤也。”格敏生襄勤,桐城方氏一般的世泽又极长,当时人多
以为盛德之报,陈康棋记此,自亦有此意;不过以六十一岁的老人,而能悬崖勒马如此,足见体格健全与神志完整的程度要高出常人之上;此种身心的强固是必有其遗传的根据的,从这方面来解释方氏的世泽以
及一般故家大族的世泽,岂不是愈于阴德果报之说?方恪敏公的例子可以说属于第二流。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馀矣,
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壁,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
鬻之。然在其家时,枕衾狎呢,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莫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媪私泄之,实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
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生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豭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奇
创.古所未闻”此例就不属于三流中的任何一流了。不过,此人性能虽已就衰,不能不以幼女做对象,
而一般的血气当健旺,神志亦尚完整,才有这一番智虑,才干放浪之中尚能有一二分制裁的力量。纪氏从
道德的立场,认为“此种公案,竟无以断其是非”;译者以为霭氏如果知道这例子,从性心理学的立场怕
的相同,有时相反的情形也可以彼此和协,不过只是性情的投合还嫌不够。见解、兴趣与才能的投合也是极关重要的。性情的不同,例如一个内向(introvert),一个外向(extrOvert),也许是和谐而相辅相成的,也许比性情的相似和反应的相同更可以促进婚姻的幸福。不过要此种幸福的长足进展与长久维持,趣味与才能的相投也是极基本的,而所谓相投自然也不一定非相同不可。一方不爱好音乐,而一方则专心致志于音乐,这大概是不容易调和的;政治的见解不同,即使性的关系很和合,怕也不一定能维持长久的美满。至若宗教的信仰完全不合(例如罗马式的天主教和福音主义的耶稣教),则婚姻决无和乐之理,无论如何应以不缔结为是。应知在今日的时代,做妻子的已经不止是一个纯粹的家庭的员司,她多少总有一些家庭以外的兴趣,所以对于外界社会生活里各种较大的活动与潮流,双方理应有些共同和相似的见解,只要大处相同,细节不同,就不要紧,所持的原则同,方法不同,也就不要紧,但若大处和原则上便有冲突,婚姻生活就难期美满。
不过我们总需记住,对于任何一桩婚事的事前的一切劝告多少总有几分臆断与预料的性质,未来是否一定成为事实,是谁也不敢断定的。一对当事人,尤其要是很年轻的话,是会因发展而随时变迁的,今天这样,明天就不一定这样。埃克斯纳(Exner)说得好:“从心理的立场来看婚姻,把婚姻当作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格关系看,它根本是一个造诣的过程。这种关系,这种过程,在行婚礼的时候,不一定就会发生或开始的。”①这造诣的过程也往往很慢,也许要费上好几年渐进的功夫,一种圆满的与深切的婚姻关系,即真正配叫做婚姻的婚姻关系,才有希望确立。表面上已到白头偕老的阶段,而此种关系还没有确立的例子,也所在而有。世间也有不少人,因为若干特殊的个人的原因不适宜于婚姻,而我们也便不以婚姻相劝。另有一部分人,因遗传的关系,为种种的健全起见,可以许其结婚,而不许其生育子女;对于这种人,比任何方法要高明许多的不生育的方法,是让做丈夫的接受绝育的外科手术。
也不能不承认是一个亟切元从归纳的刨例。
①译者在游学美国时,在犯罪学班上曾经单独调查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于强奸了一个十二
岁的幼女,被判了若干年的徒刑;译者特地到新罕布什尔州(NewHampshire)州立监狱里访问他几次,
从谈话中,又用“联想测验”(AssixiatiQnTest)的方法,断定他是神志不健全的。
②在刑事的案子里,这一类的例子也是不少的。译者追忆到本人幼年时所认识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是译者的一位族叔祖母的兄弟;这位族叔祖母没有后辈,和译者的家庭来往甚频,因此和她的兄弟也就相
熟。他平时做人很和蔼,作事也负责,身体也旺健,据说他能用鼻子吹箫;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说的人无
非是想形容他的血气之盛罢了。译者有一个时期许久没有见到他。忽然听说他犯了强奸幼女的罪名;又两
三年后,所说他瘐毙在县监狱里了。这样一个例子怕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老年癫狂的发作。
③关于本节,上文所已再三引过的克拉夫特·埃平的名著和舒奥诺与韦斯二氏合著的一书均可供参考。